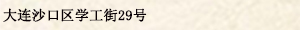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
年7月,为胡适先生开始创作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周年,为隆重纪念新诗百岁,展现海内外当代华语诗歌创作成果,北京文艺网、北京文艺网诗歌论坛、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 之间神秘关系不断追索的癖好
来源于他们。
来源于我与他们之间的隔离。
他们把这老妇人像一张轮椅
那样
制造出来,
他们把她虚构出来。
在这里。弥漫着纯白的安宁
在所有白花中她是
局部的白花耀眼,
一如当年我
在徐渭画下的老藤上
为两颗硕大的葡萄取名为“善有善报”和
“恶有恶报”时,觉得
一切终是那么分明
该干的事都干掉了
而这些该死的语言经验一无所用。
她罕见的苍白,她罕见的安宁
像几缕微风
吹拂着
葡萄中“含糖的神性”。
如果此刻她醒来,我会告诉她
我来源于你
我来源于你们
年6月
●箜篌颂
在旋转的光束上,在他们的舞步里
从我脑中一闪而去的是些什么
是我们久居的语言的宫殿?还是
别的什么,我记得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我记得旧时的箜篌。年轻时
也曾以邀舞之名获得一两次仓促的性爱
而我至今不会跳舞,不会唱歌
我知道她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瞬间
她们的美貌需要恒定的读者,她们的舞步
需要与之契合的缄默――
而此刻。除了记忆
除了勃拉姆斯像扎入眼球的粗大砂粒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不,不。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个唱和听已经割裂的时代
只有听,还依然需要一颗仁心
我多么喜欢这听的缄默
香樟树下,我远古的舌头只用来告别
年7月
●稀粥颂
多年来我每日一顿稀粥。在它的清淡与
嶙峋之间,在若有若无的餐中低语之间
我埋头坐在桌边。听雨点击打玻璃和桉叶
这只是一个习惯。是的,一个漫无目的的习惯
小时候在稀粥中我们滚铁环
看飞转的陀螺发呆,躲避旷野的闷雷
我们冒雨在荒冈筑起
父亲的坟头,我们继承他的习惯又
重回这餐桌边。像溪水提在桶中
已无当年之怒――是的,我们为这种清淡而发抖。
这里面再无秘诀可言了?我听到雨点
击打到桉叶之前,一些东西正起身离去
它映着我碗中的宽袍大袖,和
渐已灰白的双鬓。我的脸。我们的脸
在裂帛中在晚霞下弥漫着的
偏街和小巷。我坐在这里。这清淡远在拒绝之先
年7月
●活埋颂
早晨写一封信。
我写道,我们应当对绝望
表达深深的谢意――
譬如雨中骑自行车的女中学生
应当对她们寂静的肢体
青笋般的胸部
表达深深谢意
作为旁观者,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又譬如观鱼。
觉醒来自被雨点打翻的荷叶
游来游去的小鱼儿
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应当对看不见的东西表达谢意。
这么多年,惟有
这鱼儿知道
惟有这荷叶知道
我一直怀着被活埋的渴望
在不安的自行车渐从耳畔消失之际。
在我们不断出出入入却
从未真正占据过的世界的两端
年8月
●秋鹮颂
暮色――在街角修鞋的老头那里。
旧鞋在他手中,正化作燃烧的向日葵
谁认得这变化中良知的张惶?在暮光遮蔽之下
街巷正步入一个旁观者的口袋——
他站立很久了。偶尔抬一抬头
听着从树冠深处传来三两声鸟鸣
在工具箱的倾覆中找到我们
溃烂的膝盖。这漫长而乌有的行走
――谁?谁还记得?
他忽然想起一种鸟的名字:秋鹮。
谁见过它真正的面目
谁见过能装下它的任何一种容器
像那些炙热的旧作。
一片接一片在晚风中卷曲的房顶。
惟这三两声如此清越。在那不存在的
走廊里。在观看焚烧而无人讲话的密集的人群之上
年8月
●卷柏颂
当一群古柏蜷曲,摹写我们的终老。
懂得它的人驻扎在它昨天的垂直里,呼吸仍急促
短裙黑履的蝴蝶在叶上打盹。
仿佛我们曾年轻的歌喉正由云入泥
仅仅一小会儿。在这阴翳旁结中我们站立;
在这清流灌耳中我们站立――
而一边的寺顶倒映在我们脚底水洼里。
我们蹚过它:这永难填平的匮乏本身。
仅仅占据它一小会儿。从它的蜷曲中擦干
我们嘈杂生活里不可思议的泪水
没人知道真正的不幸来自哪里。仍恍在昨日,
当我们指着不远处说:瞧!
那在坝上一字排开,油锅鼎腾的小吃摊多美妙。
嘴里塞着橙子,两脚泥巴的孩子们,多么美妙
年9月
●滑轮颂
我有个从未谋面的姑姑
不到八岁就死掉了
她毕生站在别人的门槛外唱歌,乞讨。
这毕生不足八岁,是啊,她那么小
那么爱笑
她毕生没穿过一双鞋子。
我见过那个时代的遗照:钢青色远空下,货架空空如也。
人们在地下嘴叼着手电筒,挖掘出狱的通道。
而她在地面上
那么小,又那么爱笑
死的时候吃饱了松树下潮湿的黏土
一双小手捂着脸
我也有双深藏多年的手
我也有一副长眠的喉咙:
在那个时代从未完工的通道里
在低低的,有金刚怒目的门槛上
在我体内的她能否从这人世的松树下
再次找到她自己?哦。她那么小,
我想送她一双新鞋子。
一双咯咯笑着从我中秋的胸膛蛮横穿过的滑轮
年9月
●披头颂
积满鸽粪的钟楼,每天坍掉一次。从窗帘背后
我看着,投射在它表面的巨大的光与影
我一动不动。看着穿羽绒服的青年在那里
完成不贞的约会,打着喷嚏走出来
他们蹲在街头打牌。暴躁的烟头和
门缝的灯光肢解着夜色――这么多年,
他们总是披着乱发。一头
不可言说的长发!
他们东张西望,仿佛永远在等着
一个缺席者。
从厚厚的窗帘背后,我看见我被汹涌的车流
堵在了路的一侧,而仅在一墙之隔
是深夜的无人的公园。
多么寂静,凉亭从布满枯荷的池塘里冲出来
那凉亭将在灯笼中射虎:一种从公园移到了
室内的古老的游戏――
我看见我蹚过了车流,向他们伸出手去。
从钟楼夸张的胯部穿过的墙的两侧
拂动的窗帘把我送回他们中间。在二十年前?
当一头长发从我剥漆的脸上绕过
在温暖的玻璃中我看见我
踟蹰在他们当中。向他们问好。刹那间变成一群
年11月
●垮掉颂
为了记录我们的垮掉
地面上新竹,年年破土而出
为了把我们唤醒
小鱼儿不停从河中跃起
为了让我们获得安宁
广场上懵懂的鸽群变成了灰色
为了把我层层剥开
我的父亲死去了
在那些彩绘的梦中,他对着我干燥的耳朵
低语:不在乎再死一次
而我依然这么厌倦啊厌倦
甚至对厌倦本身着迷
我依然这么抽象
我依然这么复杂
一场接一场细雨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许多种生活不复存在
为了让我懂得――在今晚,在郊外
脚下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深深的、别离的小径
年12月
短诗选20首
●前 世
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
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
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
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
他哗地一下脱掉了蘸墨的青袍
脱掉了一层皮
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
脱掉了云和水
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
又脱掉了自已的骨头!
我无限誊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
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
暗叫道:来了!
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
碧溪潮生两岸
只有一句尚未忘记
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
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
说:梁兄,请了
请了――
年6月2日
●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年10月
●伤别赋
我多么渴望不规则的轮回
早点到来,我那些栖居在鹳鸟体内
蟾蜍体内、鱼的体内、松柏体内的兄弟姐妹
重聚在一起
大家不言不语,都很疲倦
清瘦颊骨上,披挂着不息的雨水
年4月
●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
面壁者坐在一把尺子
和一堵墙
之间
他向哪边移动一点,哪边的木头
就会裂开
(假设这尺子是相对的
又掉下来,很难开口)
为了破壁他生得丑
为了破壁他种下了
两畦青菜
年1月
●隐身术之歌
窗外,三三两两的鸟鸣
找不到源头
一天的繁星找不到源头。
街头嘈杂,樟树呜呜地哭着
拖拉机呜呜地哭着
妓女和医生呜呜地哭着。
春水碧绿,备受折磨。
他茫然地站立
像从一场失败的隐身术中醒来
年3月15日
●秩序的顶点
在狱中我愉快地练习倒立。
我倒立,群山随之倒立
铁栅间狱卒的脸晃动
远处的猛虎
也不得不倒立。整整一个秋季
我看着它深深的喉咙
年9月
●秋日会
她低挽发髻,绿裙妖娆,有时从湖水中
直接穿行而过,抵达对岸,榛树丛里的小石凳。
我造景的手段,取自魏晋:浓密要上升为疏朗
竹子取代黄杨,但相逢的场面必须是日常的
小石凳早就坐了两人,一个是红旗砂轮厂的退休职工
姓陶,左颊留着刀疤。另一个的脸看不清
垂着,一动不动,落叶踢着他的红色塑料鞋。
你就挤在他们中间吧。我必须走过漫长的湖畔小径
才能到达。你先读我刻在阴阳界上的留言吧:
你不叫虞姬,你是砂轮厂的多病女工。你真的不是
虞姬,寝前要牢记服药,一次三粒。逛街时
画淡妆。一切,要跟生前一模一样
年11月
●两次短跑
几年前,当我读到乔治·巴塔耶,
我随即坐立不安。
一下午我牢牢地抓着椅背。
“下肢的鱼腥味”,“对立”:瞧瞧巴大爷爱用的这些词。
瞧瞧我这人间的多余之物。
脱胎换骨是不必了。
也不必玩新的色情。
这些年我被不相干的事物养活着。
——我的偶然加上她的偶然,
这相见叫人痛苦。
就像15岁第一次读到李商隐。在小喷水池边,
我全身的器官微微发烫。
有人在喊我。我几乎答不出声来——
我一口气跑到那堵
不可解释的断墙下。
年4月
●孤峰
孤峰独自旋转,在我们每日鞭打的
陀螺之上。
有一张桌子始终不动
铺着它目睹又一直被拒之于外的一切
其历炼,平行于我们的膝盖。
其颜色掩之于晚霞。
称之曰孤峰
实则不能跨出这一步
向墙外唤来邋遢的早餐,
为了早已丧失的这一课。
呼之为孤峰
实则已无春色可看
大陆架在我的酒杯中退去。
荡漾掩蔽着惶恐。
桌面说峰在其孤
其实是一个人,连转身都不可能
像语言附着于一张白纸。
其实头颅过大
又无法尽废其白
只能说今夜我在京城。一个人。远行无以表达隐身之难。
年3月
●中年读王维
“我扶墙而立,体虚得像一座花园”。
而花园,充斥着鸟笼子
涂抹他的不合时宜,
始于对王维的反动。
我特地剃了光头并保持
贪睡的习惯,
以纪念变声期所受的山水与教育――
街上人来人往像每只鸟取悦自我的笼子。
反复地对抗,甚至不惜寄之色情,
获得原本的那一、两点。
仍在自己这张床上醒来。
我起誓像你们一样在笼子里,
笃信泛灵论,爱华尔街乃至成癖――
以一座花园的连续破产来加固另一座的围墙。
年9月
●两种谬误
停电了。我在黑暗中摸索晚餐剩下的
半个桔子
我需要她的酸味,
唤醒埋在体内的另一口深井。
这笨拙的情形,类似
我曾亲手绘制的一幅画:
一个盲人在草丛扑蝶
盲人们坚信蝴蝶的存在,
而诗人宁可相信它是虚无的。
我无法在这样的分岐中
完成一幅画。
停电正如上帝的天赋已从我的身上撤走
枯干的桔子
在不知名的某处,正裂成两半
在黑暗的房间我们继续相爱,喘息,老去。
另一个我们在草丛扑蝶。
盲人一会儿抓到
枯叶
一会儿抓到姑娘涣散的裙子。
这并非蝶舞翩翩的问题
而是酸味尽失的答案。
难道这也是全部的答案么?
假设我们真的占有一口深井像
一幅画的谬误
在那里高高挂着。
我知道在此刻,即便电灯亮起,房间美如白昼
那失踪的半个桔子也永不再回来。
年6月
●与吴少东杜绿绿①等聚于拉芳舍②
鹅卵石在傍晚的雨点中滚动。
多疑的天气让狗眼发红
它把鼻子抵上来
近乎哀求地看着嵌在玻璃中的我们
狗会担心我们在玻璃中溶化掉?
我们慢慢搅动勺子,向水中注入一种名叫
“伴侣”的白色粉末,
以减轻杯子的苦味。
桌子上摆着幻觉的假花-----
狗走进来,
一会儿嗅嗅这儿。一会儿嗅嗅那儿。
吴少东在电话另一头低低吼着。
杜绿绿躺在云端的机舱,跟医生热烈讨论着
她的银质牙箍。
我们的孤立让彼此吃惊。惯于插浑打科或
神经质的大笑,
只为了证明
我们片刻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
我们从死过的地方又站了起来
这如同狗从一根绳子上
加入我们的生活。又被绳子固定在
一个假想敌的角色中。
遛狗的老头扭头呵斥了几声。
几排高大的冷杉静静地环绕着我们
不用怀疑,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绳子终会烂在我们手中,而冷杉
将从淤泥中走出来
替代我们坐在那里,成为面目全非的另一代人。
年6月
注①:均为合肥籍当代诗人。②:咖啡馆名。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东段。
●驳詹姆斯·赖特①有关轮回的偏见
我们刚洗了澡,
坐在防波堤的长椅上。
一会儿谈谈哲学,
一会儿无聊地朝海里扔着葡萄。
我们学习哲学又栽下满山的葡萄树,
显然,
是为末日作了惊心动魄的准备
说实话我经常失眠。
这些年也有过摆脱欲望的种种努力。
现在却讲不清我是
这辆七十吨的载重卡车,还是
吊着它的的那根棉线
雨后,
被弃去的葡萄千变万化。
你在人群中麻木地催促我们
向前跨出一步。“你跨出体外,
就能开出一朵花”②。
你总不至认为轮回即是找替身吧,
东方的障眼法向来拒绝第二次观看。
我们刚在甜蜜的葡萄中洗了澡,
在这根棉线断掉之前。
世界仍在大口喘着气,
蚯蚓仍将是青色的。
心存孤胆的
海浪仍在一小步一小步涌着来舔瞧石。
我写给诸位的信被塞进新的信封
年9月
注①詹姆斯·赖特JamesWright(-),美国诗人,曾深受中唐诗人王维的影响。②引自詹姆斯·赖特的《幸福》一诗。
●忆顾准
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
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
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
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
他不会想到,
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
我们相隔39年。
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
这是一个以充分蹂躏换取
充分怀疑的时代。
就像此刻,我读着文革时期史料
脖子上总有剃刀掠过的沁凉。
屋内一切都如此可疑:
旧台灯里藏着密信?
地上绳子,仿佛随时直立起来
拧成绞索,
将我吊死。
如果我呼救,圆月将从窗口扑进来堵我的嘴
逃到公园
每一角落都有隐形人
冲出来向我问好
要么像老舍那样投身湖下,
头顶几片枯荷下下棋、听听琴?
可刽子手
也喜欢到水下踱步。
制度从不饶恕任何一个激进的地址。
年,这个火热的人死于国家对他的拒绝
或者,正相反———
用细节复述一具肉身的离去已毫无意义。
年,当河南板桥水库垮坝
瞬间到来的24万冤魂
愿意举着灯为他的话作出注释。
我常想
最纯粹的镜像仅能在污秽中生成,而
当世只配享有杰克逊那样的病态天才。
忆顾准,
是否意味着我一样的沉疴在身?
但我已学会了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
说起来这也不算啥稀奇的事儿
我所求不多
只愿一碗稀粥伴我至晚年
粥中漂着的三、两个孤魂也伴我至晚年
年3月18日
●菠菜帖
母亲从乡下捎来菠菜一捆
根上带着泥土
这泥土,被我视作礼物的一部分。
也是将要剔除的一部分:
----在乡村,泥土有
更多的用途
可用于自杀,也可用来堵住滚烫的喉咙
甚至可以用来猜谜。
南方丘陵常见的红壤,雨水
从中间剥离出砂粒
母亲仍喜欢在那上面劳作。
它又将长出什么?
我猜得中的终将消失。
我猜不到的,将统治这个乱糟糟的世界
是谁说过“事物之外、别无思想”?
一首诗的荒谬正在于
它变幻不定的容器
藏不住这一捆不能言说的菠菜。
它的青色几乎是
一种抵制-----
母亲知道我对世界有着太久的怒气
我转身打
“太好吃了”。
“有一种刚出狱的涩味”。
我能看见她在晚餐中的
独饮
菠菜在小酒杯中又将成熟
而这个傍晚将依赖更深的泥土燃尽。
我对匮乏的渴求胜于被填饱的渴求
年1月
●养鹤问题
在山中,我见过柱状的鹤。
液态的、或气体的鹤。
在肃穆的杜鹃花根部蜷成一团春泥的鹤。
都缓缓地敛起翅膀。
我见过这唯一为虚构而生的飞禽
因她的白色饱含了拒绝,而在
这末世,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
养鹤是垂死者才能玩下去的游戏。
同为少数人的宗教,写诗
却是另一码事:
这结句里的“鹤”完全可以被代替。
永不要问,代它到这世上一哭的是些什么事物。
当它哭着东,也哭着西。
哭着密室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
就像今夜,在浴室排风机的轰鸣里
我久久地坐着
仿佛永不会离开这里一步。
我是个不曾养鹤也不曾杀鹤的俗人。
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
我披着纯白的浴衣,
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
年4月
●从未有过的肢体
苹果上的虫洞必须
接受语言的责难
并非只是用刀剜去那么简单
世上最美的余荫在油锅里
医生说被截肢的病人总觉得
那段肢体
从未失去
他的手下意识地抓向那里
电击感和撕裂仍在
年4月4日张志新在狱中
用馒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
屎和尿抹在
脸上
为了阻止她叫喊
狱卒又割断了她的喉咙
在那里插入一根
生锈的铁杆
那一天我们是
完整的
我们至今仍旧完整的身体该
怎样去迎接这些残肢归来
而我们的身体也许只是虚构的
优雅的嗓子邻近耻辱
别人的残肢让我们变得谦卑
湖水,时而像油锅令人止步
年7月
●渐老如匕
一根孤而直的旧电线如何
铺展它的丰富性?
它统领着下面的化工厂,烟囱林立
铁塔在傍晚显出疲倦
乱鸟归巢
闪光的线条经久不散
白鹤来时
我正年幼激越如蓬松之羽
那时我趴在一个人的肩头
向外张望
有时,旧电线摇晃
雨水浇灌桉树与银杏的树顶
如今我孤而直地立于
同一扇窗口
看着外面依然孤而直的高压电线
衰老如匕扎在桌面
容貌在木纹中扩散
而窗外景物仿佛几经催眠
我孤而直。在宽大房间来回走动
房间始终被哀鹤般
两个人的呼吸塞满
年9月
●膝上牡丹花
年轻的值班医生对我耳语
灯下那个女人体内
胎儿早已死去
她在牡丹花布下拱起的腹部已是
一座孤坟
她轻嚼口香糖,出神盯着
帘后穿窗的飞鸟
夕光在窗玻璃上正冷却
医生想写下几句
提着笔又沉吟不定
我也曾是一座孤坟压在
母亲腰间
那令我活下来的到底是些什么
年年膝上花开,细雨中
牡丹的容颜难以言尽
今年三月,我手提锃亮的大砍刀上山
把老父坟前草木砍了个干干净净
必须写下几句来
分担此刻的缄默
呛人的青草和黏土味
即便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即便牡丹的根在那些洗白了并
永不再穿上的布衣中
已扎得那么深
年9月
●群树婆娑
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那些
正在枯萎的事物
一切浓淡恰到好处
时间流速得以观测
秋天风大
幻听让我筋疲力尽
而树影仍在湖面涂抹
胜过所有丹青妙手
还有暮云低垂
淤泥和寺顶融为一体
万事万物体内戒律如此沁凉
不容我们滚烫的泪水涌出
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
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年9月
3.
随笔炉边补
1,诗是对已知的消解。诗是对“已有”的消解和覆盖。如果你看到的桦树,是体内存放着绞刑架的桦树,它就变了。如果你看到的池塘,是鬼神俱在的池塘,它也就变了,诗性就在场了。诗即是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建成诗人的容之所,这才是真正的“在场”。
2,一首好诗,只有去路,没有来路。我们看到许多诗人在阐释,都企图将这“来路”讲清楚,瞧这是多么徒劳的一件事。写诗为世界增添神秘性,来源的混沌与爆发时的意外,是它最可爱之处。诗唯一无法解构的,是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但又必须不断地去解构。这正如诗人之手,既是建庙的手也是拆庙的手。一首好诗,甚至不需要作者。从一首好诗去追溯一个诗人,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3,一个经典作家或诗人,并非人类精神领域匮乏感的解决者,而恰是“新的匮乏”制造者。制造出新的匮乏感,是他表达对这个世界之敌意的方式。换言之,也是他表达爱的最高方式。而且,他对匮乏的渴求、甚于对被填饱的渴求。
4,诗人应该有一种焦虑,那就是对奢求与集体保持一致性的焦虑。好的东西一定是在小围墙的严厉限制下产生的。一个时代的小围墙,也许是后世的无限地基。这种变量无从把握,唯有对自我的忠实才是最要紧的。
5,语言于诗歌的意义,其吊诡之处在于:它貌似为写作者、阅读者双方所用,其实它首先取悦的是自身。换个形象点的说法吧,蝴蝶首先是个斑斓的自足体,其次,在我们这些观者眼中,蝴蝶是同时服务于梦境和现实的双面间谍。
6,诗学即是剥皮学。比如,卧室剥皮后是一条峡谷。我剥皮后是你。诗学真正令人惊异之处,不在于更复杂的“它何以是”,而只在于“它竟然是”。它抛弃了无所不能的自由,而仅让自己停留在局限的、强指的自由。不在于屎溺桌椅何以有道,而在于道竟止于屎溺桌椅。竟然是!“竟然是”的无穷乐趣。
7,我想,写诗或者写任何体裁,语言学行为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发现并爱上这个世界的神秘性。换个说法,我们唯一无法解构的也是这个世界的神秘性。比如,许多人告诉我:读不懂你的诗,其实“误读”赋予诗歌以更广阔的多义性。正是受众的误读重塑了作者。误读正是阅读的意义,也是神秘性的主要部分。
8,一个诗人对真理过度追从,部分源于他对语言的无能。在尽览语言的各种深层之妙后,诗会远离真理与谬误在分界线上的剧烈争吵。诗会远离所有清晰的界线,而只偏爱某种混沌的、令人迷醉却往往在社会规则上失准的气息。甚至谬误,时而在诗人笔下,亦让人饮之如甘泉。悖谬之途的景物同样令人沉迷,虽然它与真理一样无力绑架诗歌。谬误时而也与人的同情心聚变为某种道义之力。我宁可认为存在着一个道义与诗的结合体,而不存在一个真理与诗的结合体。
9,“谷物运往远方,养活一些人。谷物中的颤栗,养活另一些人”。
诗人正是被谷物中的颤栗养活的那些人。
10,对诗歌而言,存在四个层面的现实:一是感觉层面的现象界,即人的所见、所闻、所嗅、所触等五官知觉的综合体。二是被批判、再选择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即“各眼见各花”的现实。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中国本土文化,其实是一种包含着浓重超现实体的文化,其意味并不比拉美地区淡薄,这一点被忽略了,或说被挖掘得不够深入。每个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逝去的部分”。如梁祝活在我们捕捉的蝶翅上,诸神之迹及种种变异的特象符号,仍存留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四是语言的现实。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主导的缺陷性过渡,在百年内又屡受政治话语范式的凌迫,迫使诗人必须面对如何恢复与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这个问题,这才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如果不对现实二字进行剥皮式的介入,当代汉诗之新境难免沦入空泛。
11,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必然地在各种镣铐与限制之中,对立由此产生,在我看来,“对立的意愿”与“意愿的对立”是所有艺术的根源。我同时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解决这种对立,有时,恰需深化这种对立,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强的动力。文学不会死于它无力帮助人们摆脱精神困境,而恰会死于它不能发现、不能制造出新的、更深的困境。困境之存,诗性之魂魄也。伟大的写作者奔走于“困境接续”的途中,而不会长久陷于写作的技术性泥潭。此困境的巨大语言镜相,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群峰连岳。
近期展读链接: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向以鲜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麦城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杨克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杨卫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高世现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道辉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旺忘望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臧棣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吉狄马加篇
北京文艺网纪念新诗百年特辑|当代诗人名家近作展读:于坚篇
回复“百年新诗”,即可查看往期内容。
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吗杭州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