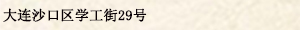陈先发九章系列诗选
街头即绘
那令槐花开放的
也必令梨花开放
让一个盲丐止步的
却绝不会让一个警察止步
道一声精准多么难
虽然盲丐
在街头
会遭遇太多的蔑称
而警察在这个国度,却拥有
深渊般的权力
他们寂静而
醒目
在灰蒙蒙的街道之间
正午
花香涌向何处不可知
悬崖将崩于谁手不可知
年3月,选自《不可说九章》
群树婆娑
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那些
正在枯萎的事物
一切浓淡恰到好处
时间流速得以观测
秋天风大
幻听让我筋疲力尽
而树影仍在湖面涂抹
胜过所有丹青妙手
还有暮云低垂
淤泥和寺顶融为一体
万事万物体内戒律如此沁凉
不容我们滚烫的泪水涌出
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
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年9月,选自《杂咏九章》
良愿
不动声色的良愿像尘埃
傍晚的湖泊呈现靛青色
鸟
在低空划着线条
鸟被它自己的线条勾勒出来
快得只剩下一个轮廓
枯苇,咔嚓一下
在耳朵的深处折断
这一切其实并不值得写下
淤泥乌黑柔软
让我想起胎盘
我是被自然的荒凉一口一口喂大的
远处
夸张的楼群和霓虹灯加深着它
轻霜般完美
轻霜般不能永续
年7月,选自《斗室九章》
箜篌颂
在旋转的光束上,在他们的舞步里
从我脑中一闪而去的是些什么
是我们久居的语言的宫殿?还是
别的什么,我记得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我记得旧时的箜篌。年轻时
也曾以邀舞之名获得一两次仓促的性爱
而我至今不会跳舞,不会唱歌
我知道她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瞬间
她们的美貌需要恒定的读者,她们的舞步
需要与之契合的缄默――
而此刻。除了记忆
除了勃拉姆斯像扎入眼球的粗大砂粒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不,不。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个唱和听已经割裂的时代
只有听,还依然需要一颗仁心
我多么喜欢这听的缄默
香樟树下,我远古的舌头只用来告别
年7月,选自《颂九章》
黄鹂
用漫天大火焚烧冬末的
旷野
让那些毁不掉的东西出现
这是农民再造世界的经验,也是
梵高的空空妙手
他坐在余烬中画下晨星
懂得极度饥饿之时,星空才会旋转
而僵硬的死讯之侧
草木的弹性正恢复
另有一物懂得,极度饥饿之时
钻石才会出现裂隙
它才能脱身而出
她鹅黄地、无限稚嫩地扑出来了
她站不稳
哦,欢迎黄鹂来到这个
尖锐又愚蠢至极的世界
年1月,选自《裂隙九章》
老藤颂
候车室外。老藤垂下白花像
未剪的长发
正好覆盖了
轮椅上的老妇人
覆盖她瘪下去的嘴巴,
奶子,
眼眶,
她干净、老练的绣花鞋
和这场无人打扰的假寐
而我正沦为除我之外,所有人的牺牲品。
玻璃那一侧
旅行者拖着笨重的行李行走
有人焦躁地在看钟表
我想,他们绝不会认为玻璃这一侧奇异的安宁
这一侧我肢解语言的某种动力,
我对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两个词(譬如雪花和扇子)
之间神秘关系不断追索的癖好
来源于他们。
来源于我与他们之间的隔离。
他们把这老妇人像一张轮椅
那样
制造出来,
他们把她虚构出来。
在这里。弥漫着纯白的安宁
在所有白花中她是
局部的白花耀眼,
一如当年我
在徐渭画下的老藤上
为两颗硕大的葡萄取名为“善有善报”和
“恶有恶报”时,觉得
一切终是那么分明
该干的事都干掉了
而这些该死的语言经验一无所用。
她罕见的苍白,她罕见的安宁
像几缕微风
吹拂着
葡萄中“含糖的神性”。
如果此刻她醒来,我会告诉她
我来源于你
我来源于你们
2010年6月,选自《颂九章》
稀粥颂
多年来我每日一顿稀粥。在它的清淡与
嶙峋之间,在若有若无的餐中低语之间
我埋头坐在桌边。听雨点击打玻璃和桉叶
这只是一个习惯。是的,一个漫无目的的习惯
小时候在稀粥中我们滚铁环
看飞转的陀螺发呆,躲避旷野的闷雷
我们冒雨在荒冈筑起
父亲的坟头,我们继承他的习惯又
重回这餐桌边。像溪水提在桶中
已无当年之怒――是的,我们为这种清淡而发抖。
这里面再无秘诀可言了?我听到雨点
击打到桉叶之前,一些东西正起身离去
它映着我碗中的宽袍大袖,和
渐已灰白的双鬓。我的脸。我们的脸
在裂帛中在晚霞下弥漫着的
偏街和小巷。我坐在这里。这清淡远在拒绝之先
年7月,选自《颂九章》
卷柏颂
当一群古柏蜷曲,摹写我们的终老。
懂得它的人驻扎在它昨天的垂直里,呼吸仍急促
短裙黑履的蝴蝶在叶上打盹。
仿佛我们曾年轻的歌喉正由云入泥
仅仅一小会儿。在这阴翳旁结中我们站立;
在这清流灌耳中我们站立――
而一边的寺顶倒映在我们脚底水洼里。
我们蹚过它:这永难填平的匮乏本身。
仅仅占据它一小会儿。从它的蜷曲中擦干
我们嘈杂生活里不可思议的泪水
没人知道真正的不幸来自哪里。仍恍在昨日,
当我们指着不远处说:瞧!
那在坝上一字排开,油锅鼎腾的小吃摊多美妙。
嘴里塞着橙子,两脚泥巴的孩子们,多么美妙
年9月,选自《颂九章》
滑轮颂
我有个从未谋面的姑姑
不到八岁就死掉了
她毕生站在别人的门槛外唱歌,乞讨。
这毕生不足八岁,是啊,她那么小
那么爱笑
她毕生没穿过一双鞋子。
我见过那个时代的遗照:钢青色远空下,货架空空如也。
人们在地下嘴叼着手电筒,挖掘出狱的通道。
而她在地面上
那么小,又那么爱笑
死的时候吃饱了松树下潮湿的黏土
一双小手捂着脸
我也有双深藏多年的手
我也有一副长眠的喉咙:
在那个时代从未完工的通道里
在低低的,有金刚怒目的门槛上
在我体内的她能否从这人世的松树下
再次找到她自己?哦。她那么小,
我想送她一双新鞋子。
一双咯咯笑着从我中秋的胸膛蛮横穿过的滑轮
年9月,选自《颂九章》
泡沫简史
炽烈人世炙我如炭也赠我小片阴翳清凉如斯我未曾像薇依和僧璨那样以苦行来医治人生的断裂我没有蒸沙作饭的胃口也尚未产生割肉伺虎的胆气我生于万木清新的河岸是一排排泡沫来敲我的门我知道前仆后继的死必须让位于这争分夺秒的破裂暮晚的河面,流漩相接我看着无边的泡沫破裂在它们破裂并恢复为流水之前有一种神秘力量尚未命名仿佛思想的怪物正无依无靠地隐身其中我知道把一个个语言与意志的破裂连接起来舞动乃是我终生的工作必须惜己如蝼蚁我的大厦正建筑在空空如也的泡沫上
年8月,选自《拉魂腔九章》
萤火虫
正阳关乡亲们认为含冤
而死的人会变成萤火虫
我看见墓碑群集之地
敝败的门户上
荒滩苇丛烧成的
灰烬中
萤火虫漫天飞舞
弱者胸中可怕的缄默
死后仍存有一丝力气把
这小灯笼点亮
这难免让人心安
有时一只萤火虫猛地
撞在我脸上
它们
想说些什么?
传说中有穷人家的孩子
捉来一袋萤火虫借光而读
从一张白纸上突然显出的字又
说些什么?
大坝日复一日涌起
我高高卷起的裤脚上
露水如电
炙热的晚风请
不要停下来。我尝到强权苦涩
手持大棒的恶棍们,请不要停下来!
这萤火虫彻夜而舞
滚滚而来的两岸因它们的
幽暗之光
因这鸡鸣和乳汁得以永固
年8月,选自《拉魂腔九章》
秋江帖
去年八月,在江边废弃的小学校
荒凉的味道那么好闻
野蒿壮如幼蟒
一堆堆垃圾像兽类残骸
随手拍一下,旧桌子便随着
浮尘掩面而起
二楼窗外正是江水的一处大拐弯
落日血色均匀的巨型圆盘
恰好嵌在了凹处
几根枯枝和
挖掘机长长的黑臂探入盘内
——仿佛生来如此
我想,在世界任何一处
此景不复再见
寥寂如泥
涂了满面
但世界的冲动依然难以遏止:
灰鸥在江上俯冲
黑孩子用石块在攻击我的窗户
孩子们为何总是不能击中?
他们那么接近我的原型
他们有更凶悍的部队和无限的石块
潜伏于江水深处
我知道数十年后
他们之中,定有一人将侵占
我此刻的位置
他将继承这个破损的窗口继承窗外
又聋又哑的好世界
这独一无二的好世界
年10月,选自《寒江帖九章》
江右村二帖
草木也会侵入人的肢体
他将三根断指留在了
珠三角的工厂
入殓前,亲人们用桦枝削成新的手指——
据说几年前
人们用杉木做成脑袋为
另一个人送葬
语言并不能为这些草木器官
提供更深的疲倦
田垄上,更多幼枝被沉甸甸的
无人采摘的瓜果压垮
我们总为不灭的炉膛所累
草木在火中
噼啪作响
那些断指的、无头的人
正在赶回
母亲的米饭已在天边煮熟
年10月,选自《寒江帖九章》
暴雨洗过敬亭山
竹笋裹着金字塔胀破雨后的
地面,把我从这嫩黄棺椁中剥出来的
是我自己的手。让我陷入绝境的
是我自己的语言
面对众人我无法说出的话
在此刻这幽独中仍难表达
我踱步,在自己危险的书房里
像辨认山林暝色中有哪些
埋不掉的东西。是死者要将喉中
无法完成之物送回地面
这雨滴。这寂静
这绵绵无尽头的延续
遍及我周身。遍及我痛苦阅历中的
每一行脚印,每一个字
年8月,选自《敬亭①假托兼怀谢朓九章》
崖边口占
闲看惊雀何如?
凌厉古调难弹。
斧斫老松何如?
断口正是我的冠冕
悬崖何时来到我的体内又
何时离去
山水有尚未被猎取的憨直
余晖久积而为琥珀
从绝壁攀援而下的女游客
一身好闻的
青木瓜之味
年8月,选自《敬亭①假托兼怀谢朓九章》
枯树赋
上山时看见一株巨大枯树
横卧路侧
被雷击过又似被完整地剥了皮
乌黑喑哑地泛着光
我猜偷伐者定然寝食不安
但二十人合围也不能尽揽入怀的
树干令他们畏而止步
在满目青翠中这种
不顾一切的死,确实太醒目了
像一个人大睁着眼睛坐在
无边无际的盲者中间
他该说些什么
倘以此独死为独活呢
万木皆因忍受而葱茏
我们也可以一身苍翠地死去
我们也可用时代的满目疮痍加上
这棵枯树再构出谢朓的心跳
而忘了有一种拒绝从
他空空的名字秘密地遗传至今
年8月,选自《敬亭①假托兼怀谢朓九章》
在火锅店论诗中
杯斛鼎沸的火锅店忽然闯入了
一只蝴蝶
这让交谈有了难度
它转眼又不见了
它斑斓的苦笑在空气中却经久不散
蝴蝶并非假象,但在
下一句中它必成假象
而且很不幸
在一瞬间我甚至看到了
蝴蝶的三面:它的疲倦,它的分裂和
它最终的不可信
一个以经世务实为耀的
国度又为何如此热衷于
谈论虚无的蝴蝶?
有一天我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到
它的泪水
心头一阵紧缩
像烈日下神秘的沥青在流动
那些血的镀锌管里
亿万只风格各异的
红灯笼在流动
如此精微之物难道搞不清我们
生而为人的泪水究竟源于何处?
它依然穿梭于梦的门轴
去完成一些
我们无法预知的事情
对此二者:臆想的蝴蝶与我们
可触可摸的蝴蝶
之间的微妙缝隙
我们依旧阐释不能,描绘
也不能——
我也依然认为文学应脱胎换骨于
这样的两难之境
为此我们向庄子举杯
也向纳博科夫举杯——他或许是
既钻研了人类不幸又深临了
蝴蝶深渊的唯一一位
甚至,为了抚平我们
他在蝴蝶灰烬中创造了永恒的洛丽塔
年5月,选自《遂宁九章》
渺茫的本体
每一个缄默物体等着我们
剥离出幽闭其中的呼救声
湖水说不
遂有涟漪
这远非一个假设:当我
跑步至湖边
湖水刚刚形成
当我攀至山顶,在磨得
皮开肉绽的鞋底
六和塔刚刚建成
在塔顶闲坐了几分钟
直射的光线让人恍惚
这恍惚不可说
这一眼望去的水浊舟孤不可说
这一身迟来的大汗不可说
这芭蕉叶上的
漫长空白不可说
我的出现
像宁静江面突然伸出一只手
摇几下就
永远地消失了
这只手不可说
这由即兴物象强制压缩而成的
诗的身体不可说
一切语言尽可废去,在
语言的无限弹性把我的
无数具身体从这一瞬间打捞出来的
生死两茫茫不可说
年3月,选自《不可说九章》
冷眼十四行
夜雀滑向池中橘红的圆月
静穆的阴影投射在平面上
负责阐释一切阴影的
年轻禅师觉得疲倦——
他为不能平息在词句中
变幻不可控的语调难堪
也为活在一个看不到起点和
终点的暗哑的世界难堪
他知道沉默不可完成
而自我又永难中断
他为一棵樱桃树难堪
为樱桃的不可中止难堪
他看见死者仍在弧线上运动而
每一块湿润的石头都如梦初醒
年3月,选自《茅山①格物九章》
岁聿其逝
防波堤上一棵柳树
陷在数不清的柳树之中
绕湖跑步的女孩
正一棵棵穿过
她跑得太快了
一次次冲破自己的躯壳
而湖上
白鹭很慢
在女孩与白鹭的裂隙里
下夜班的护士正走下
红色出租车
一年将尽
白鹭取走它在世间的一切
紧贴着水面正安静地离去
年1月,选自《裂隙九章》
不可多得的容器
我书房中的容器
都是空的
几个小钵,以前种过水仙花
有过璀璨片刻
但它们统统被清空了
我在书房不舍昼夜的写作
跟这种空
有什么样关系?
精研眼前的事物和那
不可见的恒河水
总是貌似刁钻、晦涩——
难以作答。
我的写作和这窗缝中逼过来的
碧云天,有什么样关系?
多数时刻
我一无所系地抵案而眠
年1月,选自《裂隙九章》
深嗅
油菜花伏地而黄
有人伫立
不语
这个时代灌注给一个旁观者的
厌倦有多深
取决于这种最熟悉的花在我
每一侧面的崩溃
还将持续多久
转眼即见破碎如同我
无法统一自己
反过来的结论也成立吗?
“无为”二字在雨中闪光
葛洪医生,
请修补我!
这花瓣会交出一个新的入口?
当我和我体内的
废墟
深深地
嗅着它
我体内的蓬头垢面嗅着它
我身上每一种失败
涌回来
从器官的无数缺口中
嗅着它
毕生在泥土中奔命却从未深俯于
一朵花的老妈妈
怀揣着远未出生的我
也奋不顾身前来
嗅着它
年3月,选自《茅山①格物九章》
在永失中
我沿锃亮的直线由皖入川
一路上闭着眼,听粗大雨点
砸着窗玻璃的重力,和时光
在钢铁中缓缓扩散的涟漪
此时此器无以言传
仿佛仍在我超稳定结构的书房里
听着夜间鸟鸣从四壁
一丝丝渗透进来
这一声和那一声
之间,恍惚隔着无数个世纪
想想李白当年,由川入皖穿透的
是峭壁猿鸣和江面的漩涡
而此刻,状如枪膛的高铁在
隧洞里随我扑入一个接
一个明灭多变的时空
时速六百里足以让蝴蝶的孤独
退回一只茧的孤独
这一路我丢失墙壁无限
我丢失的鸟鸣从皖南幻影般小山隼
到蜀道艰深的白头翁
这些年我最痛苦的一次丧失是
在五道口一条陋巷里
我看见那个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慢慢走过来了
两个人脸挨脸坐着
在两个容器里。窗玻璃这边我
打着盹。那边的我在明暗
不定风驰电掣的丢失中
年5月,选自《遂宁九章》
膝上牡丹花
年轻的值班医生对我耳语
灯下那个女人体内
胎儿早已死去
她在牡丹花布下拱起的腹部已是
一座孤坟
她轻嚼口香糖,出神盯着
帘后穿窗的飞鸟
夕光在窗玻璃上正冷却
医生想写下几句
提着笔又沉吟不定
我也曾是一座孤坟压在
母亲腰间
那令我活下来的到底是些什么
年年膝上花开,细雨中
牡丹的容颜难以言尽
今年三月,我手提锃亮的大砍刀上山
把老父坟前草木砍了个干干净净
必须写下几句来
分担此刻的缄默
呛人的青草和黏土味
即便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即便牡丹的根在那些洗白了并
永不再穿上的布衣中
已扎得那么深
年9月,选自《杂咏九章》
秋兴九章
二
钟摆来来回回消磨着我们
每一阵秋风消磨我们
晚报的每一条讣闻消磨着我们
产房中哇哇啼哭消磨我们
翠花消磨着我们
弘一也消磨我们
四壁的霉斑消磨着我们
四壁的空白更深地消磨我们
年轻时我们谤佛讥僧,如今
不过加了点野狐禅
孔子、乌托邦、马戏团轮番来过了
这世界磐石般依然故我
这丧失消磨着我们:当智者以醒悟而
弱者以泪水
当去者以嘲讽而
来者以幻景
只有一个珍贵愿望牢牢吸附着我:
每天有一个陌生人喊出我的名字
三
这个怪癖持续多少年了?妈妈在
阳台上为牡丹剪枝,总要颠来倒去地
唠叨父亲那几句遗言。
比如,不要用火把去烧蜘蛛
这一类话,多为父亲临终前高烧的谵语
另外他告诫我不要激怒乞丐与
僧人----
我怀疑父亲曾短暂拥有这两个身份。
他第一次讲这话时,是我十六岁那年夏季
高考刚结束
我们一块儿蹲在皲裂的湖底闷头抽烟
那时,谁的话我也听不进
只想一个人
远走他乡
哪怕在一座外省的监狱中悄悄死去。
我从不回应父亲的话。我们仰着头
看荒苇摇曳
大片越冬的灰鹤缓缓踏过乳白色天空。
妈妈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么多年过去
她的剪刀咔嚓咔嚓地愈加锋利
我看见牡丹在逃离----
许多个傍晚
偶然射来的车灯突然照亮她的半边脸
她瘦削的肩膀抖动着
她俯下身去
我深陷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件不是牡丹的事物里
九
远天浮云涌动,无心又自在。
秋日里瓶装墨水湛蓝
每一种冲动都呈锯齿状
每一个少年都是情色的天才
为了人的自由,上帝活在他自己强设的模型中
每一棵树都在盲目闪着微光
每一片叶子都在吐着体内致幻剂
我们忍不住冲到路上
却依然无处可去。偶然性像一场大病无边无际
我们中有人疯掉了,不再拘于形迹
他们唱歌自觉得是山楂树在歌唱
他们睡觉自觉得是小河水在睡觉
他们疯掉了而我依然清醒得像“吊灯里的巨蟒”
傍晚蜘蛛群悬于网上
灰颈鹤在芦荡中聚集
泉水正赶往低处汇合
我们追逐的东西却依然无始无终
文字狱内人满为患证明我们
尚未失去一切;学究们对我的荒诞破口大骂
也说明我尚未被彻底掏空
只有这两样,配得上这明净的秋天
来来来,为这余烬中的种子干一杯
为这世上的种种不可能干一杯
为我从镍币的正反两面都能
找到快乐了干一杯。为我体会了镣铐中的空和
六和塔上的空,这两种空,为这可悲的渐悟干一杯
年10月,选自《秋兴九章》
陈先发
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年)、《前世》(年)、长篇小说《拉魂腔》(年)、诗集《写碑之心》(年)、随笔集《黑池坝笔记》(年)、诗集《养鹤问题》(年台湾版)、《裂隙与巨眼》(年)等。曾获奖项有“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年——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年中国年度诗人”、“年至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首届袁可嘉诗歌奖、天问诗歌奖、中国桂冠诗歌奖、年桃花潭国际诗会中国杰出诗人奖、陈子昂诗歌奖、安徽文学奖等数十种。年与北岛等十诗人一起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新诗贡献奖”。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等多种文字传播。
请扫描下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