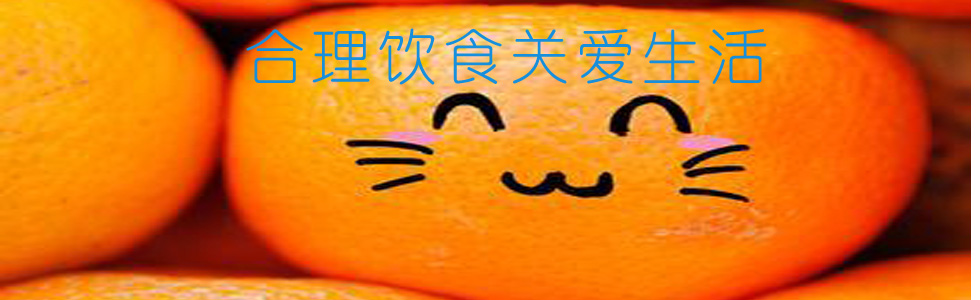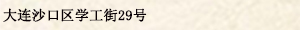考完了,考上了,一切都好了吗文末有获
有这样一段经历,
浸透着汗水,在记忆中深深铭刻,
直至几十年后回首,
仍能清楚记得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
有这样一个名词,
见证过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
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高考!高考!
首先,小编祝所有高考的同学考出好成绩!
祝所有高考的同学考出好成绩!
祝所有高考的同学考出好成绩!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还记得之前《新侨艺报》发出的高考的征集号令吗?
我们收到了来自摄影爱好者、学校老师、家长投稿的
各种关于高考的故事、物品以及考场照片
获奖名单和奖品在文末公布
一场考试,到底能改变多少命运?
年冬天,全国万来自车间、田野、军队的年轻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其中27万人后来走进大学,被培养成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一场考试,就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
转眼40年过去,虽然高考制度早已不像当年那样理所当然、万众期待,虽然“指挥棒”下的教育模式、命题思路和招生办法已累积了大量不同的声音,虽然时代变了,在市场大潮冲击下,人们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但不容否定,高考本身,依然带给人希望和念想。
又到一年高考季,一次考试,到底能给一生带来多大的影响?一个分数,究竟能不能决定命运的走向?这并不是眼前就能回答的问题,但站在40年的岁月长河里,细看那些普通人被高考改变的人生轨迹,依然能发现一些端倪。
“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那束光”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年的夏秋之交悄悄流传起来的。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形容,这一信息,“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人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那一年,后来成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楼亿平17岁,在余姚丈亭赵家大队“支农支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砖窑厂挑砖、晒砖,沉重的担子压在稚嫩的肩上,平淡而艰辛的时光像砖块一样日日叠加,她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所以,当妈妈在电话里告诉她高考恢复的消息的时候,这个从小在海曙城区长大的少女忍不住喜极而泣。
那一年,后医院肾病泌尿中心主任医师的沈志久19岁,在老家北仑区东南部的梅山岛当“赤脚医生”,收入不错,但隐隐总有些不甘心。所以,当郭巨中学的金龙土老师走遍郭巨、峙头和梅山,挨家挨户地通知动员学生去参加高考时,虽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沈志久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楼亿平和沈志久分别考上了杭州大学和温州医学院,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毫无疑问,最先走进大学的这批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作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同时,“隧道尽头的那束光”还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
年,在农村插队3年的西安人滕占卫名落孙山。第二年,他拼了全力,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宿舍就紧闭房门,灯下苦读。
隔了这么多年,回忆起当年的高考经历,滕占卫脑海中闪过的最初影像不是书山题海,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以及麦田里那个弯着腰挥汗如雨的少年。
6月中旬,他刚刚花半个月的时间,抄完一本政治复习资料,还没来得及背下来,就被老实守旧的父母赶回田里。家人觉得,考大学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如老老实实收麦。
“一言不发地从早干到晚,没有人比我卖力,看起来我是多么热爱割麦啊,只有我知道自己多痛恨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因为只有割完,才能回去复习。”他说。为了把耽搁的时间补回来,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复习到凌晨2点,早上6点起床,一边跑步一边背诵。那是他每天最享受的一段时光。
年秋天,他终于如愿走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门。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学生的年纪从十多岁到三四十岁不等。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后,一段新的人生开始了……
“命运的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分配”。沈志久如愿进了医疗系统,楼亿平进了浙江省旅游局教育科,滕占卫更幸运,没费任何周折,他就被分配到当时西安的东方机械厂,进的是“轻松又干净”的技术部门。
这一家国营厂,厂区占地几万亩,员工超过万人。家属区就像一个镇,里面的学校、医院、商店,应有尽有。
这里几乎包办了每个员工的生老病死:吃饭在单位食堂,医院,身上穿的是厂里发的工作服,孩子上的是子弟学校,都不需要花钱。虽然每月工资不到50元,但这些福利很让他的同学们眼红。
年高考准考证。邱伟钢提供
也正因如此,“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在偏僻的农村、山区、海岛,再贫穷的家庭都会千方百计地送孩子上学。有着30年教龄的宁波中学外语教研组组长郑军老师当时还在舟山岱山县大衢中学读高中,简陋的教室里,老师反反复复地强调,如果不想像爷爷爸爸那样天天在海上捕鱼,那只有考大学一条路。
海岛上的中学是村民的希望和主心骨,每天清晨,当学校的铃声响起,孩子们相互叫唤着在黎明的晨曦中向学校走去开始一天学习的时候,很多村民也依着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孩子的成绩,是辛苦劳作背后最大的盼头和念想。
郑军那年高考没完全发挥好,但也考上了杭州一所大学的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回岱山,在母校教书。他把自己未能完全实现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师生几乎同吃同住在一起,他们班教室的灯,常常是最晚一个关的。孩子们也争气,他带的第一届学生,就有好几个考上了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名校,成为这个偏僻海岛上的传奇。
教学生涯里,郑军印象最深刻的是届的一名学生,父亲因为海难去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印象中,这个瘦弱、单薄还有些内向的大男孩每天的午餐只有自己带的一点鱼干。但是,他目标明确、踏实努力,那一年高考以全省文科70多名的成绩考上了人民大学。更难得的是,进入名校后也没有松懈,拿回了一张又一张的荣誉证书。郑军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每一点进步——视野越来越开阔,性格越来越阳光,谈吐越来越自信,一所好的大学真的能把人变得越来越出色。
10多年的时间,这个青涩的渔村男孩成长为成熟的知名律师。郑军看在眼里,高考,大概是这个孩子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吧。
年高考准考证。邱伟钢提供
“原来人生那么长”
从一个好的大学,到一个好的工作,很多人认为,那就是一辈子了。
“我当时怎么会想到,人生那么长。”当年的“天之骄子”滕占卫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滕占卫和老婆孩子蜗居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个房子是一名同事让给他们住的。
刚进厂的年轻人不能马上分到房子,得排队等。一晃10年过去,他去工厂房管处一看,自己前面还有几百人。
现在回过头来,滕占卫觉得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就耽搁了。“我一直活在大学生的优越感里面,每天准点上班、下班,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不去思考,也不去关心这个封闭系统外的变化。就像做了个梦,醒来什么都不是了。”
这10年,正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思想变化最大的时候,个体户越来越多了,最受推崇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万元户”,“下海”成了最流行的词。他们这家以前“削尖了脑袋”都难进的国营大单位,效益却每况愈下,不再“吃香”了。
很多福利取消时,夫妻感情开始出现裂痕。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了,父母年纪大了,菜买贵了一点,要吵;给哪家老人钱多了一点,也要吵;妻子说你看谁谁现在都有车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每天在家里算怎么回事,“战争”一触即发……
后来同事要收回房子,妻子一下子变成了“泼妇”,她一手抓着门框,一手叉着腰,气势咄咄逼人:“我不会走的,有种你们来搬。你们搬哪里,我就睡哪里!”
等众人散去了,她的力气仿佛一下子被抽干,坐在床上,眼泪掉下来:“弄到这一步,日子没法过了。”
房子没有让出来,但这次闹得全厂皆知的争吵,成为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没多久,滕占卫离婚了。年,36岁的他辞去工作前往广东东莞,成为浩浩荡荡南下打工族的一员。
年高考文化考试复习提纲。邱伟钢提供
同样是那十来年,楼亿平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
被分配到省旅游局教育科后,她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年被抽调到浙江大学当英语老师。年因为教学成绩出色,被公派到加拿大交流一年。一年后有个政策,就是把公派费用还上后,可以留在国外继续读书。
经过艰难的抉择,楼亿平决定放弃国内已有的一切和安稳的生活,从头开始。
国外的教育部门当时并不承认国内学历,从年开始,楼亿平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重读大学本科。公派费用取消了,生活费没有着落,楼亿平每天在食堂打工、在图书馆兼职,给老师抄材料……终于读完本科、硕士、博士,之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去了美国。
转眼就到了上个世纪末,改革的春风最早吹到的珠三角,滕占卫凭借着技术优势顺利在一个家用电器厂找到工作,月薪多元,是以前的10倍。工厂男女不例不到1:4,他很快就找了个漂亮的打工妹做妻子。当“春天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时,已到不惑之年的滕占卫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春天”,又回来了。
在此同时,舟山的小岛上,郑军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送进大学,送进更大的世界。自己也没有放弃过努力,年,他从岱山调到宁波中学任教。
“永远不要想着高枕无忧”
年,高校扩招,录取率翻倍,高考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年,教育部开始推行自主招生,结束了此前高校只能在每年同一时间招考的历史……除了考场上取得的一个“裸分”之外,影响录取的因素越来越多了。
刚刚调到宁波中学的郑军很快就发现了海岛学生和城市学生的不同,海岛上学生的家庭背景都差不多,城市里却千差万别。
班里条件比较差的是下岗工人的孩子,郑军给予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