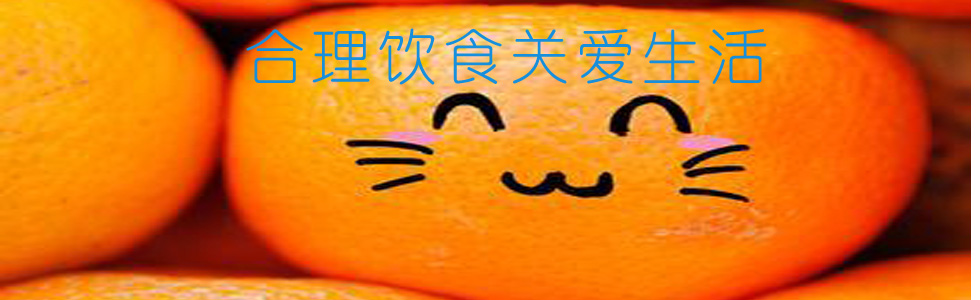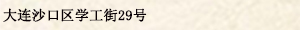台州江海行丨台州海难备忘
丨水的凶险丨
台州海难备忘录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孙金标/摄
10月28日晚,台州外海域,“浙岭渔”渔船与希腊籍油轮“南极光”号发生碰撞。
在30万吨级的油轮面前,这艘来自温岭的渔船,如同巨兽脚前的蚂蚁。在吨位悬殊的对抗中,渔船遭遇灭顶之灾,船体沉入海底,6名船员全部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失联船员当中,3人是温岭籍渔民,2人为陕西人,1人为湖北人。这一夜,遇难的船员沉浸在海水中,船员的家属,也全部都沉浸在泪水中。
在台州的海域范围内,这样的海上事故,每年都会发生。据海事部门统计,年到年间,台州辖区共发生各类等级的海上事故件,死亡人,沉船艘。
与陆地上的事故相比,海上一旦翻船,救援人员往往受距离、天气、通讯等限制,无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落水的船员,除了救生衣,别无依靠,独自面对汪洋大海,有多少生还的概率?
海的凶险,渔民最清楚
温岭石塘粗沙头村的码头入口,张贴着一则“寻尸启事”。
时间正是午后,渔运船停靠岸边,鱼贩子的卡车陆续到来,工人们忙碌在鱼筐中间,对海货分类挑拣。
往来的人们,都注意到了“寻尸启事”,有的会凑近看内容。
“启事”要寻找的,是一位掉海失踪的渔民。他生前的照片,以及姓名、穿着、失踪海域位置等信息,都详细地印在上面,末尾附有家人的联系方式,和“重金酬谢”字样。
“找不到的,大海茫茫,哪里找得到。”和我并排站着的一人看着“启事”说道。
“既然找不到,为什么还要贴启事呢?”我问那人。
“大概是家人还抱着一丝侥幸吧。”他说,渔民一生在海上漂泊,却希望死后能入土为安,倘若在海上遇难,这样的愿景,便很难达成,“我有三个亲人,捕鱼为生,都死于海上,其中两个人的尸体也未能寻着。”
我与他攀谈起来。
他叫阿彪,38岁,石塘人,家族里多是渔民。
三十年前的冬天,阿彪刚读小学,一日放学回家,他得知,自己的三姨父和一船人去海上捕鱼,再也没回来。
姨父水性很好,跳入水中,能一口气潜游一百多米,他不敢相信姨父会出事。
过了一个月,舟山的渔民在海上发现了两具姨父同船人的尸体。两人捆在同一块木板上,身上都穿着救生衣。
“姨父的船,估计是在舟山外海沉的,船员落水后,两两捆绑在一起,等待救援,只是冬天海水太冷,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姨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当时才一岁半,此后,三姨一人将孩子们抚养长大。
年,阿彪在温岭太平工作。那年,他的大表哥,驾驶木船捕鱼回家时,溺水而亡。人们找到他时,发现身体焦黑,猜测是他游泳碰到了海底电缆,触电导致休克后溺死。
一年半后,阿彪的二表哥出海捕鱼,整船人都失踪了。“失踪那天夜里,风平浪静,别艘船正用对讲机与我二表哥的船联系,突然信号断片,之后再也联系不上了。”阿彪说,二表哥所在的船,是坚固的钢制渔船,事发时并未说船进水,“渔民们推断,排除被海生物袭击的可能,这艘渔船应该是撞上了大型商船,连船带人沉入海底。”
大海瞬息万变,渔民出海捕鱼,本就冒着生命危险,阿彪说,自己胆子小,从此断了出海的念头。
台州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海难
渔民的死亡,仅让人窥得海之凶险的冰山一角。当大海在一瞬间,吞噬数十条生命时,才会引起全社会的警醒。
把时间向前推移20年。在三门县蛇蟠山以东海域,一艘载客船翻沉,导致55人死亡,11人失踪。
年2月9日,离农历小年夜还有两天。当天上午8时,隶属三门县航运公司的“浙三机3号”客船,从象山石浦客运码头,驶往三门海游客运码头,途中停靠象山县高塘乡三门口码头。这艘载了76个人和不少货物的客船,离开三门口码头时超载。
当天风平浪静,船以平常速度往南行驶。值班驾驶员杨善友在驾驶室掌舵。他的儿子坐在一旁,跟着学开船技术。
开到途中,杨善友让出了驾驶位置,让儿子来开一段。他想着自己就在边上,万一有什么意外,再把控便是。
船行驶到蛇蟠山东面海域,杨善友儿子眼见前方有一张渔网,便向右急打船舵。此时,客船发生了较大的左倾,横浪打来,海水进入了船的左舷。
船里的旅客们慌乱了,他们奔到了右舷一侧,放置在顶棚的货物也向右滑移。整艘船向右严重倾斜,很快便翻沉了。
沉船时,部分人员跳海逃生,有10人被附近作业的渔民救起,其中2人救起时已死亡。另有2个水性好的,游到岸边生还。驾驶员杨善友在事故当中溺亡,客船船长陈尚德因找不到尸体,被判定为失踪。
这起沉船事故,被认定是一起因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而引起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
除了这起事故之外,台州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大的翻船事故,是在年3月1日,“金清轮”船因超载,在椒江口沉没,死人。
海上事故发生的规律
台州市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高级海事调查官张文敏,对年以来的海上事故进行了统计总结,并从中发现一些规律。
“事故发生区域相对集中。”张文敏说,诸如海门港区附近水域,头门、大(小)竹山附近水域,石塘-松门一带水域及以东航路附近水域,大陈岛附近及以东的水域,大麦屿周边水域等五片区域,都属事故多发地带,90%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这些水域。
易发生事故的船舶,以吨及以下的小型船舶为主,且造成死亡失踪人数、沉船艘数较多。外地船舶在台州海域内,也容易发生事故,统计期内有44.25%的事故主体是外地的船只。
海上事故种类中,碰撞、触损、自沉、触礁等四类,占到了事故总数的95.21%,其中碰撞类事故达件,是最易多发的事故种类。
“碰撞类事故里,渔商船碰撞事故占全部事故的25.68%,占所有碰撞事故中的52.08%,比例很高。”张文敏说,10月28日温岭渔船沉船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渔商船碰撞事故,“碰撞的原因,也由多方面引起。”
大型货轮、邮轮的航道,都是南北走向的,而台州渔船外出捕鱼则是东西走向,航道呈交叉状,在非禁渔期间,商船航道上可能存在着大量的渔船。
台州渔民的航行专业素质与安全意识普遍不高,有些喜欢抢大船船头,有些对国际避让规则不了解或不遵守,有些会在雾天冒险航行,有些在夜间无证驾驶,加之通讯不在一个频道,渔商船相遇难以交流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相互间碰撞时有发生。大型商船的吨位,是渔船的成百上千倍,商船会在毫无知觉中撞沉渔船。
每到休渔期,张文敏都会受邀去给渔民上培训课。课堂上,他会将这些事故发生规律,总结给在场的渔民听,并嘱咐他们提高警惕,熟练掌握驾驶技能,事故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
“好在近年来,渔船的装备逐渐提高,渔民对于海上安全方面的意识也在慢慢树立。”张文敏说,从事故的年份表上看,年发生53起事故达到峰值,之后几年事故数量基本稳定在了每年十几起。
台州海上搜救能力正稳步提升
海上一旦发生事故,就需要有外来力量,对遇难人员、船舶、货物进行救助。施行救助的力量,可以来自政府,也可以来自社会民间组织。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海上救助,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体系。美国的海上执法机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拥有强大的海空立体救助能力;日本的海上应急技术先进,能对进入其领海的任何船舶和其他航行设备实行全天候监控;英国90%的海上搜救,依靠皇家救生艇协会(RNLI)负责实施,这是一个自愿组织机构,所有的运行费用均来自社会捐助。
中国是海洋大国,要发展海洋经济,健全海上救助体系尤为必要。台州作为国内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海上救助能力已走在全国前列。去年,台州海上搜救中心共成功救助遇险人员人、遇险船舶18艘,水上人命救助成功率达97.2%。
“海上救助能力,关键体现在密度和速度上。”台州市海事局政委兼党委副书记叶兴良说,台州辖区的海上搜救可调控力量,既有各级海事部门的几十艘巡逻艇,还有以“平安水鬼”郭文标为代表的几支民间搜救队伍,保证了搜救的密度。
“由交通运输部全额投资1.2亿元的大陈岛海事工作码头,将于明年动工,该码头能停靠吨级的驱逐舰,主要作用就是海上救助。”叶兴良说,“十三五”期间,在大鹿岛、头门岛也将建设类似的码头,“往后,海上事故一发生,我们的救援队伍就能从最近的码头出发,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此外,台州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工程,也经交通部审查同意,将于不久后启动。设备库建成后,能对海上溢油事件进行应急处理,保护海洋环境。
“‘十三五’之后,台州的海上救助能力,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叶兴良说。
本文参考文章:《航海技术》年第六期《论安全意识教育在船员培训中的重要地位》
郭文标:一身本领,只为多挽救一条命
本报记者包建永/文孙金标/摄
12月16日,初冬的早晨。走在温岭市石塘镇小沙头村的海边,海货下船,渔民们忙着分拣。岸边屋舍的墙壁上,零星贴着“寻人启事”“寻尸启事”的黑白纸。
郭文标的家就在海岸边不到十米的地方。这是他的家,也是他自费设立的海上救助站基地。各家的渔船在他门前下货,停泊,他自家的船只能停在百米外的水中。
从前,他是职业渔民,如今,他是专门负责义务救人的“平安水鬼”。30多年来,他从东海的波浪里共救回了多条生命。
救命不谈价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郭文标接到一个救助电话。
一艘渔船在海区发生动力故障,船员被困在船上两三天。船员四处求救,但没人去救。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救人容易,救船难。如果救人,开一艘小艇去,就能把人接上岸。但是,渔民把船看得跟命一样重,人在船在,他向你求救,就是请你既救他的人,也救他的船。两三天耗下来,没人去,最后找到了郭文标。
别人不愿做的事情,郭文标没有推辞。12月15日早上,郭文标挂了救助电话后,便派手下救助队员开着拖船去救人救船。直到16日下午,才把故障船拖到岸边。来回行程超过20个小时。
郭文标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出海一次,油费近元/小时,这样一个来回,不算人工成本,光油费就耗去了2万元。
虽然如此,郭文标只要接到类似的救助电话,照样去救;只要他去救,从来不跟被救者谈价格。
他最多是提醒被救渔民,如果船有保险,保险赔偿可以补偿给救助队(其实,绝大多数保险赔偿都远远低于拖船成本),如果没有,拉倒。如果渔民拿到保险赔偿后不愿抵偿救助费用,郭文标也没办法。
“总不能向人家讨要啊。”他说,“要不然老百姓都来骂我了,你郭文标不是无偿救人吗?怎么又收费了?”
郭文标说,救人本来就是自愿的,事后跟被救者谈救助费,就有违初衷了。
他从小在海边长大,爷爷、父亲都是渔民。渔民生活苦,他深有感触。小时候,他曾亲眼看到,门外海面上,船翻了,船上的人抱着桅杆,慢慢随桅杆一起沉下去。他眼睁睁看着生命消失,却毫无办法。
如果自己有能力救人,那该多好。
13岁那年,他和几个渔民在台风中把小船拉到沙滩上。一个60多岁的老人没站稳,跌进海里。他立即跳下水去,凭一己之力把老人救上来。
这是他人生里从水中救起的第一个人。从此之后,他救人的数量逐年累加。救人的本领,也越来越高。
年冬天,风大浪急,海水冰凉,一艘渔船在松门东面海上沉了。郭文标和海事部门人员开救援船去救人。当时,浪头四五米高,有一人抱着逐渐下沉的桅杆,绝望地望着救助人员。郭文标跃入巨浪,犹如水中游龙,潜到被困人员身边。海事人员抛来缆绳,他接在手里,在自己手臂上缠绕几圈,再把缆绳绑到受困者身上,让救援人员把受困者先拉上去。然后,他自己再上救援船。第一次看到他在如此恶劣天气里救人的海事人员,都看傻眼了——平安水鬼,名不虚传。
根据统计,只要郭文标赶到事故现场,落水者被发现时还活着,无一例外,都能被他救起。
救人多了,郭文标的名气越来越大,河里的、水库里的落水事故,都打电话向郭文标求助。只要力所能及,他从不推辞。
“活人永远有路走,死了什么都没了。”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海上救助站
在水中救人这件事上,郭文标从来没有停步过。
年,他筹资万元,建造了专门用于海上远距离救助的“浙岭渔”号船,成立省内首家海上平安救助站。
截至目前,他救助遇险船舶多艘,救助遇险船员多人,海上救助船舶用时达多小时。
鲜为人知的是,他有一支跟了他20多年的救助队伍,至今共有16人,最小的33岁。这些救助队员大多是他的亲戚,有亲家,有妹夫。
海上救人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只有信得过的人,才会跟他一起干。比如妹夫毛礼荣,就是海上救人的一把好手。他和郭文标既是亲戚,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他1.8米的个子,多公斤,人高马大,身手敏捷。他和郭文标一起开快艇出海救人,落水者在他手中就像小鸡一样,一抓一提一放,落水者瞬间转到船上,救人效率非常高。
这么一支高效、庞大的队伍,维持正常运行需要一笔不菲的支出。郭文标说,自己可以不领工资,但队员都有家庭要照顾,不能不领工资。他算了一笔账:16名救助队员一年工资万元;目前共有5艘船,基本维护成本一年30万元;一年中出海救人总耗油二三十万元。
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解决?像其他渔民一样捕鱼肯定不行。人在远洋作业,万一急救电话来,就来不及回援。“我接到求救电话后,要确保10分钟内能出海”。因此,为了确保救人效率,郭文标已经多年没有出海捕鱼了。
他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开办休闲渔业。除了“浙岭渔”号救助船,他还陆续增添了4条休闲渔船。在有急救任务时,休闲渔船参与海上急救,在无急救任务时,休闲渔船从事创收。“往年休闲渔业每年能收入三四十万元,今年最好,收入七八十万元。”
同时,政府每年也对他有数十万元的补助。
一边无偿救人,一边哭穷,不算好汉。郭文标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强造血功能,解决救助队伍的运行资金问题。
正是通过这些努力,这些年来,他在海上救人这件事上,丝毫不打折扣。
当然,救人过程中,也有让他生气的时候。
今年10月,在温州某海域,一船员的腿断了,家属打电话向郭文标求救。郭文标问明情况后,第一时间携医生开快艇赶到事发海域,却怎么也找不到人。他电话打给伤员,打不通,又打给家属,家属说已经叫飞机接走了。
事后说起,郭文标仍抑制不住情绪:“人接走了也不告诉一声,白白浪费资源。”
他尊重每个求助者,也希望求助者及其家属给予基本的尊重。
珍重每条命
在救援过程中,误解、迁怒、无理要求的事情,郭文标都碰到过。
比如,在年5月的一次救援过程中,郭文标和救助队员在海里外的洋面连续多天搜救,找回六具尸体,另有一人怎么也找不到。沉船拖到岸边,家属认为他救人不尽力,群起殴打他。后来警察赶来了,事态才得到控制。
又比如,有船员在海上心脏病发作,电话打到郭文标这里。他问明情况后,携医生开船过去。医生经过检查后,表示病人不行了。病人的儿子见状,立刻反目,骂郭文标见死不救,拍他照片,扬言要曝光他。郭文标很无奈。
对于这些意外的“打击”,郭文标表示都能理解。他说,只要自己尽所能去救人,就无愧于心,其他的不必太在乎。
渔民习惯把海上漂尸称为“元宝”,把尸体捡回来,送到岸上,称为“捡元宝”。
郭文标“捡元宝”的数量,也不下三位数。
“救活人上船,接死人回岸。活人感谢你,死人保佑你。”他说。在他眼里,“捡元宝”和救活人一样,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海民“捡元宝”还有许多讲究,比如必须男尸俯、女尸仰才可以捡,否则不吉利。碰到男尸仰和女尸俯的情况,郭文标会对尸体说,带你回家,尸体会翻过来。“外人或许觉得我们迷信,但是我们海边人就信这个,事实也是这样的。”他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人套着救生圈漂浮在海上,他过去一看,已经没呼吸了。他下水,用绳子捆绑死者腰身。在他穿绳过腰的时候,死者一把抓住绳子,不放手。郭文标轻声对他说:“你松松手,我带你回家。”死者把手松了。
许多人把他当作保护神,但他更希望每个人都重视自己的生命,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现在渔船作业人员中,80%以上是农民工。这些船工没培训、没证书、技术差、经验少,许多事故是因为外行造成的。
还有,按照国际惯例,海上风力超过7级的,政府不出海搜救。而事实上,许多触礁、抛锚、发动机故障等事故,都是发生在风大浪高的恶劣天气里。
“海上救援,限制条件很多,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郭文标希望,“活着的人,都懂得惜命。”
八百里海塘:
阻挡潮水的“海上长城”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江竹铭/图
台州依山濒海,海岸线绵长,常受台风、海潮侵扰。
智慧的台州先民们,在海岸边筑起了一道名为“海塘”的屏障,向外防潮御咸,向内积蓄淡水,保一方安宁。
历史上,海塘曾一次次被风雨摧毁,又一次次被修复,“海上长城”般模样的背后,是台州人奔竞不息的围垦精神。
历史上,海塘屡建屡毁
据史料记载,台州的第一条海塘“健阳塘”,位于健跳(今属三门县),堤长约丈,为唐代诗人怀玉所建。这条海塘屡屡决堤,于南宋端平年间(年-年)重新修筑。
宋代时,台州筑建海塘的规模逐渐扩大。玉环楚门筑起樊塘,三门浦坝港沿岸的沿赤、花桥、小雄等地先后筑有七处海塘。宋嘉定十五年(年)黄岩知县蔡范筑县塘35公里。
元代至正年间(年-年),温岭境内自马盘山东抵松门筑有萧万户塘。楚门一带也建起了灵山塘、能仁塘等四处塘坝。
椒江境内的第一条海塘,是明代弘治年间(年-年)所建,这条“丁进塘”位于海门至横街一线古沙堤附近,长约30公里,个别地段与古沙堤重合。正德年以后,椒江、温岭、三门等地又先后筑有海塘。
清代至民国年间,三门湾沿岸筑起10多处海塘;临海在杜桥、桃渚修建25公里的海塘;三甲至金清一带围筑了汤塘,绵延20多公里;温岭与玉环也在东南沿海地带建了几十处海塘。
古时修筑海塘,都是断断续续,所建地点也零星分散。塘坝几乎都是泥土筑成,偏于低矮单薄,形状也弯曲不齐,一旦遇到大潮狂浪的袭击,便决堤成灾,这对于沿海居住百姓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新中国建立后,台州各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沿岸人民群众,结合海涂围垦,新建海塘堤坝,并对其不断加高加固。台州湾南岸的金清、三甲海塘,从七塘筑至十塘,速度与规模均前所未有。到年末,台州已有第一线海塘堤条,全长公里,有效地保护起沿海地区的百万居民。
大灾过后,台州修筑高标准海塘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塘虽在数量上颇具规模,但防御能力并不强大。海塘裸露在外的三面墙体,缺乏有效保护,一般只能抵御十年一遇的海潮。当威力超强的海潮袭来,这些“赤膊塘”往往不堪一击。
现已退休的台州市水利局原农村水利管理处处长金良耀,回忆起年第11号台风登陆时的景象,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台州境内的公里海塘,几乎全线崩溃,大水淹没了台州城。”
水灾过后,人们拥向海塘,做堤坝修复工作。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一条位于椒江岩头闸外、长约2.05公里的山东石塘,完好无损。
“这条海塘,曾毁于号台风,椒江区政府斥巨资,以抵御五十年一遇海潮的标准,进行重新修建。”金良耀说,用砌石与混凝土进行加高、加固后的海塘,扛住了汹涌的海潮攻击。
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建高标准堤塘,势必还会陷入“年年来台风,年年修堤塘,年年遭毁坏”的恶性循环,经济损失将更加严重。台州市委市政府铁了心:一定要修筑高标准海塘!
建设海塘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历经灾难的台州人,此时显示出了众志成城。无论是市委机关干部、社会企业,还是农户村民,纷纷主动捐款,为塘坝添一块石。
此后五年时间,台州对多公里的塘坝进行重新修筑。其中有公里,可抵御五十年一遇的海潮,有70公里可抵御二十年以上的海潮。此外,为了保护台州主城区不受潮水侵害,椒江外沙海塘按照百年一遇的标准设计。
“高标准海塘建成后的几年,台州又遭遇了‘云娜’‘麦莎’等强台风侵袭,海塘安然无恙,潮水再也没有进来。”金良耀说。
海塘的另一面
据水利部门统计,截至年底,台州市共有标准海塘公里,其中在建海塘48公里,二线海塘54公里,一线海塘公里,一线海塘防潮标准大部分为五十年一遇。
近年来,台州市在省政府部署下不断开展强塘工程,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海塘除险加固。年到年,累计投入资金7.57亿元,新建和加固海塘近公里。
对于居住在海塘周边的百姓们而言,这条长长的堤坝,不仅仅只是一堵抵御潮水的墙。
农户在海塘内外搞起了养殖。譬如三门沿海的塘坝内,有许多养殖户开辟青蟹、白虾养殖基地。温岭石塘、松门海塘外的一大片滩涂,也被附近农户承包下来,用于蛏子、贝壳的养殖。
塘坝也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如椒江的江滨公园,就是建在海塘之上,公园里还有一座浙东千里海塘纪念碑,已成为城市地标性建筑。市民在茶余饭后,去塘坝上走走,也是不错的选择。
临海白沙湾的湖景公园,在设计中将海塘与公园结合起来,今后这里将开发水上娱乐项目,把海塘与旅游业结合起来。
刊于《台州日报》12月23日4-5版
编辑丨张莉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