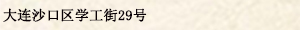蜜蜡情史小说连载和你做爱是因为我爱你
蜜蜡不敢张了眼睑定睛看他——怕清醒了一场欧泊舶来的梦——听着欧泊走至床前,她抬了指尖去探,却没见手臂穿过那虚空的影像,只触到绵软的粗布和实在的肌体,接着腕子被捏起轻轻放回原处:“手带着点滴,就别动啦,会回血的。” 原来是——嗯——哦,天河。 天河掇过条凳子坐了,徐徐向杯里吹凉,小小纸杯在那粗涩指节间像玩具。蜜蜡于是说我不喝水,天河好玩地笑:“不是给你,我喝,跑着来的,干死我了。”咕咚咕咚两大口,被烫得咳出好大动静,半晌又说,“我外地演出去了,你病了怎么不联系我啊,我好来照顾你啊——噢对,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哈,我这思维都惯性了,觉得咱俩早就特熟呢。” 蜜蜡不解:“可你怎么进来的,我出痘子——”“还不多亏了我妈!”他走去把个本子取来,“我妈她老人家,医院看了几十年的病,最自豪的业绩就是这个,喏,精装病历。”蜜蜡看时,是本硬纸封面的病历,脊上用蜡线装订得结实,打开来,日期、病史、医院、诊断医师,一页页记载得整齐,还小心粘贴了当时开出的处方。“我妈把照得着的亲戚朋友,都建了档了,这本是我的。还非逼着我身边带着,我老大不愿意的,你说,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哗啦哗啦翻出一页指给蜜蜡:“不过今个我妈可真格立功了。这一篇,有理有据地向护士小姐证明了我的水痘病史,我才能这么光明正大地进来看你,嘿,医院,就是骨质疏松,一套护肤精华就搞定了——”天河一拍脑门,“扯远了扯远了,总之一句话,一直到你出院——”又捶胸口,“都有人照顾你了——诶没液了,我给你拔针,放心,啊,家有大夫,我是科班出身,咱轻轻的——” 蜜蜡看着他极娴熟地揭开胶布,按好了棉球顺血管方向利索地一抽:“按着吧,我给你弄个橙子。”翻箱倒柜地拿了刀子橙子,汁水四溢地刚切了一个,蜜蜡哧儿笑了:“你杀橙子呢。把床柜瓷碗里我那把勺子拿了来吧。” 蜜蜡把橙子蒂部挖个盖子,掀开,勺子插进去,两个弧度正好咬合,撬了八撬,橙皮便如脱衣一般褪了。蜜蜡捧给他,一边眼波转转:“笨的。吃果子非用刀么。很多种果子不用刀吃得更好呢。” 天河拿过那橙皮端详,浑然一张整的,脸上疑惑转为轻叹:“吃了无数回橙子,这个吃得最有趣儿!原来女孩子可以巧到这宗儿啊。” 他笑意盈盈地去看蜜蜡,却见刚还亲静明媚的那女孩一瞬换了风韵,变得亮烈难犯了。 “谢谢来看我,橙子请你吃,吃好请回吧。”
莫名其妙的天河走得郁闷,蜜蜡却怎么也没心思理会。 人的记忆就是这么奇怪,像海洋上破碎的岛屿,会因为天边偶尔现出的几片黛青影子,而回想起它所漂离的那块大陆来——蜜蜡的苦痛常在于此。 橙子稀松平常,偏牵扯着蜜蜡心房最不易挪动的一块砖石,轻轻一碰就要从心底痛上来。 蜜蜡的挖橙子,是欧泊教的。不只橙子,欧泊似乎懂得种种讨巧的法子。比如,欧泊会把西瓜挖了瓤切进大碗,在上班前放进小冰箱里淬着,等午睡醒的蜜蜡找来吃;又会顺手翻翻装了奇异果的篮子,找一枚熟软的切开来,取小勺给蜜蜡,你一半我一半舀冰淇淋似的慢慢吃;蜜蜡买失败的草莓,酸涩得只能扔掉,欧泊却懂得半杯酸奶两勺糖地做成草莓酪——欧泊笑起来像小孩子,采访写稿时就是硬冷的男人,闲暇当口又甚至会带了主妇的色彩:欧泊手头看着的书时而会是专讲烹调的,还有他洗熨衬衫的样子。 欧泊的房间常常整齐,床单也是按时换洗的,蜜蜡又想起欧泊站在那儿,拿了喷气熨斗,认真地烫他半新的羊毛外套,一边还说:“我爸告诉我,独自生活很久的男人,岁数大一些的就会整洁。蜡蜡觉得我老吗?”蜜蜡于是好笑地笑,然后摇头。 欧泊死的时候,不到27岁,是蜜蜡快18岁的春天,但蜜蜡不觉得欧泊老。甚至没想过欧泊生于她的上一个十年。有篇东西,大意是女人希冀的那一类理想男人会有些什么特点,内容浪漫有趣,“下雨天背我过积水,并说我可以再重一点”、“女秘书要给他缝上脱落的扣子,他说谢谢不用”之类的。其中还有一条是“和孩子在一起是孩子,和成人在一起是成人”,蜜蜡看过,觉得这写的就是欧泊了。 欧泊的孩子气,有时会以俏皮的程度爆发一下。蜜蜡想起初春里,她把面掉的苹果搁置一旁同时说,“不脆的苹果就像蜡呢,甜味都给盖掉。”欧泊从书堆里抬起头,有所思地看着她,倏尔淘气地笑,把苹果切了两半,拿了勺子一层层刮。苹果面了,松软地落下在小碗里,是不沾不连的果松。欧泊扔掉果皮壳子,去抱个不大不小的纸盒来,一边得意地说,“销价买的刨冰机!同事说我冬天买这个傻气,今天派用场,我请蜡蜡吃冰。”又去厨房,伴随着开箱柜的声音,“我的砂糖和沙拉酱呢?” 面前摆好两碗果松冰沙,剔透地沁着凉气,蜜蜡执了勺要尝,却被欧泊想起什么地把碗罩住:“慢着,对了——”他转身去翻月历,盘算着又说,“蜡蜡,是在每月十号变脾气吧。今天二十五号,嗯,偶尔吃点凉,没事,好,吃吧。” 蜜蜡一边吃一边好笑:“我真会变脾气嘛?!” …… 其它记忆,到来的时候,是种心很疼的悦暖,橙子却不是。 想起的时候,橙子就只是心很疼。 因为蜜蜡的初夜,沾着橙的清香。
当年,以蜜蜡十几岁眼睛的观察,心理的观照,她认为不会有太多女孩会把处女的身体,真正留到新婚那夜——尽管那是美梦,却是太过纯洁得吹弹即破——于是一直,蜜蜡安谧地等待欧泊。但是,欧泊竟然一直同样安谧:很多夜,睡前,欧泊都是热热地看看蜜蜡,然后关掉灯,在黑暗中背对她,换了洗得白白的T恤,掀开被子抱她入怀,徐徐睡去。爱蜡蜡,却连吻都很少。 有一回,蜜蜡被欧泊看到手中的健康杂志,翻开在男性疾病的一章,欧泊愣一下,随后爆出满满的大笑。后来,欧泊扳住蜜蜡的肩,看住她认真地说:“蜡蜡,我没病,别乱想。”可蜜蜡无法不乱想。她少有地疑惑和好奇了。 两人的第一夜到来得格外的晚,在相识快两年,蜜蜡17岁的尾巴上。 那年入冬最大的一场雪,从黄昏开始下的,阻挡了晚饭后的散步——不加班的日子,欧泊必要蜜蜡一起的功课。蜜蜡调笑欧泊老爷爷气很重,欧泊耸眉:“动动健康。况且我也不信蜡蜡真的会不胖。就这样吃和不动。”“就是不会胖嘛。”蜜蜡撇嘴,脚下赶一步挽了他一起走。 那晚欧泊有闲,却不能散步,冷,蜜蜡早早捂进被里,抱了一篮橙削着,又在膝上放了大碗接那汁水。欧泊看她耍杂技似地擎着那碗,就笑了,走来说:“笨的。吃果子非用刀么。很多种果子不用刀吃得更好呢。” 欧泊料理橙子,蜜蜡看得高兴了,拿过来学,撬了一个个,总没欧泊弄出的完整流畅。欧泊又笑:“蜡蜡蛮得活像小牛了!都不着巧劲儿的。”在蜜蜡身后坐了,环住她帮她找角度,冒出胡茬的下巴蹭着蜜蜡脸颊。 一刹,欧泊不动,也不说话了,蜜蜡扭回头看他,被欧泊捞住颈子,在嘴唇上吻住了。橙的香气凉沁沁地撒了满床。 蜜蜡一直想那天自己是什么样子。不记得有没有搽香水了。也不记得是不是把头发放了下来。甚至不记得以哪种姿态让欧泊看住了。不过一定很骚——这字眼总是烫的,后来的日子,只要想起,就在蜜蜡脑里烙一下:咝一声,欢愉的焦痛。 过程一直完美。结束就不是。给她温了水擦洗时,蜜蜡发现欧泊哭了——泪少得刚打湿眼眶,那一种压抑却酸痛到她眼里,于是她安慰他:“我不疼,你很轻的。” 欧泊深深看她一眼,轻轻抱起她,气息埋在她发里:“蜡蜡,对不起……” 直到离世,欧泊都是起初那个欧泊,好得一如既往。蜜蜡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不起,可欧泊的对不起,却一直惴惴的,放不下。
就是这样放不下。橙的回忆起始,蛰伏已久的往事重又破土而出,不再是蜜蜡费力控制的暗涌,欧泊的所有铺天盖地,白茫茫掩住一切。 在个月亮极白的深夜,蜜蜡从又一个欧泊的梦里惊醒,枕上凉凉,眼前黑黑,窗里投影进来树的怪影,门外静得夜都要吞掉。蜜蜡赤脚跑过光色苍青的走廊,打电话找托帕。 应的竟是女声。纤柔里一种愠怒。 “是他的病人——托帕找给我。” 电话被扔开,听得女声微微细细一句,“瞎忙的事情总挂满一尾巴,拎不清!”复接起。 “蜡蜡!”托帕说话带着鼻音,微喘着,“在哪儿?” “走廊里。手机被他们收去了。”蜜蜡深吸了气,“对不起。扰到你们了。” “没事。小海明天休假,来住一晚。”隐隐听得托帕说“小海。先睡。一会儿陪你。乖。”,然后走出来,“蜡蜡,出什么事儿了?” “有一个人,天河,他有些像欧泊。” 托帕用了些时候弄懂蜜蜡,换了缓缓的口气讲给她:“蜡蜡,你觉得回忆欧泊会弄疼你,所以强制自己不想他,可越是这样,你就越想他。这折磨了你,是不是?” “嗯。就像薛西弗斯。一直要推巨石上山,却总被它滚下来,碾得生疼。” “蜡蜡!你这是……”托帕犹豫怎么说话。 “我知道你迟疑什么。咨询师不能对病人说病理的:病情会严重。”蜜蜡追上一步,“不过我和别人不是一样。我要解释,解药,简单直白说了就好。” “嗯……你知道薛西弗斯,一定能了解他为什么作为了强迫症的代名词。——在你心里,一直存在强迫回忆的问题,现在,类似的人和事出现,就成为加重问题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问题,公认的治疗方案是森田疗法。” “怎么做?” “如果我没猜错,你对那个你认为像欧泊的人,不理睬了吧?”蜜蜡沉默。托帕接着讲下去,“应该顺应自然。不逃避。这就是所谓的森田疗法了。逐渐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在不伤害欧泊的情况下,开始新的爱情,与之并存的婚恋心理障碍,自然能打开。做到很难,但是蜡蜡,你是很特别的女孩子。我相信你——” “——你到底还睡不睡觉了!”突如其来女人的怒音,是海蓝宝。 托帕闷闷挂了,留下蜜蜡枯坐了半夜,一时脑里现出欧泊的音容,一时又想起天河每每来探时的状貌,又把金发晶的劝念了几遍:“已经两年多了!就是守寡也够意思了!欧泊肯定也不愿意你为了他这样发神经的!……”就这样任由各式的思绪摇来撞去,额头疼的,心下却缓缓平和了,倦意也来到,睡眠好了许多。于是暗叹托帕的锐利。 次日天河又来,依旧端了书给她讲故事,一边还翻往后面看写些什么,蜜蜡见他性格急到这般模样,却还能一字一顿恳切地念,有些好笑有些感动:“为什么讲这本给我呢?”“《金银岛》嘛!美国电影里孩子生病了都念这个。成人童话!你肯定也爱听。” 蜜蜡开心,笑起来:这男人,当她是孩子来疼呢。又慨叹多久没笑得这么舒心了。 天河念毕一章来看蜜蜡,发现她并不像往常那样眼睛空空,而是盈盈地望向他,心里一热:“你不生我气了?”“我并没有生过你的气呢。”“那——” 蜜蜡抿了眼睫,又是一笑:“在想自己的事情。就要想清楚了。” 恋着的人儿笑得这般动人,天河几乎不能自持,把她的手一拉,很想在那微鼓的腮线上亲一亲,又怕僭越了她,只好抚抚落在枕上的发丝:“我想给你洗头发,行不?” 天河的手指穿过头发触到肌肤时,有那么一刹那,蜜蜡再次错觉到这是回到了从前。欧泊轻轻地撩起水,揉着她的发,和她交谈,为她洗掉思想里积压很久的疼痛。 有些释然,不会再那么难过,而是品尝过去,带来的幸福感。蜜蜡宁愿相信,天河,是欧泊的思念带来的人。
快出院的一天,蜜蜡斜靠在床头,膝上摊开几张黑胶唱片,听天河放唱机——天河扛个焦黑喇叭,提着这老式唱机走进病房时着实吓到了她——又问他:“怎么会有这个的?”天河很有些得意:“你忘了我学作曲的?我特喜欢这些东西。很不容易找了买到的。”他在唱机内盖里找了一阵,拣出一张,“听这个,张君秋的《女起解》。很棒,唱机放出来京戏的感觉CD转录不出的。” 轻轻放上去,点上唱针,咿呀唱起来。戏文蜜蜡听不大清,唱腔却还华美,所以听得还算享受。 正唱到“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楼下一阵喧嚷,就听得有人倔倔喊蜡蜡!蜡蜡!,蜜蜡到窗前一看,竟是金发晶,正和门房吵闹,一蹦一蹦地向前,旁边是痞子哥哥拦着,赶忙推开窗户喊她。 金发晶立即招手,喊着:“蜡蜡!你寝室说你住院了!病了也不叫我来!这老头不让我和我哥进!”又扭回头向着门房,“你!不讲理啊,我们要进去!” 天河目光问着,蜜蜡就说是好朋友,外地来看我的,这可怎么好。天河就拿了东西要走,一边回头说句:“我问过护士,你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就能和朋友一起了,先安排他们住我那儿,你别管了。” 晚间天河又来,告诉蜜蜡金发晶住好了。蜜蜡看他眉眼里情绪还没褪去,想一定是又被金发晶审了很多话,就说:“晶晶就是嘴厉害,人很好。”天河开解地笑:“你朋友活泼得很啊。很可爱。” 妈妈来看蜜蜡,恰好碰上蜜蜡出院的日子。 天河带着金发晶来接,正在收拾东西,妈妈在门口叫声蜡蜡,急切切的。蜜蜡带了责备的眼神看金发晶——金发晶低眉顺眼的:“听说你病了我着急嘛。正好阿姨来看我,就……”
“要不是晶晶我现在还不能知道,你这孩子。很久不回家,病了都不告诉妈妈。”妈妈嗔着,捧了蜜蜡的脸颊,上下端详,“还好,没瘦。”自然又看天河,妈妈聪明的眼睛含着笑容:“谢谢你照看好我们蜡蜡。”天河点头叫阿姨,又把妈妈和蜜蜡比对了两眼,说:“阿姨真年轻!蜜蜡是美女一点不奇怪。”蜜蜡觑他一眼:“妈妈,他是天河,在我们学校读音乐硕士的。哦,叔叔呢?”“车里呢。我叫他赶紧回来的,昨晚刚到的家,外地进货去了。” 天河拎了东西招呼说:“阿姨,咱们走吧,下午一起吃饭。”妈妈连连摆手:“不行,你还读书呢,让叔叔请。”“没事阿姨,我在职的,嘿嘿,还挣外快。应该的,别客气了。” 晚上蜜蜡要和妈妈一起睡,妈妈就在学校招待所开了个套间,天河掏押金,被叔叔拦住了。 叔叔去洗澡,妈妈拉着蜜蜡在里间坐下,眼圈红了。蜜蜡伸手去展妈妈眼角:“妈妈别哭,出皱纹的。妈妈这么漂亮的眼睛。”“蜡蜡,是妈妈不好,应该再多些儿给你电话,就不会连你生病也不知道了——店里实在忙。妈妈有点儿不舒服,前两天起不来,要不一听晶晶说就得来看你的。”蜜蜡连忙照着亮看妈妈:果然,妈妈气色苍白,嘴角也憔悴地垂着,一阵揪心的内疚,赶紧问什么病。 起初妈妈一直只说伤风发烧,后来蜜蜡不信得生了气,才说:“蜡蜡早是大人了。妈妈告诉你,你别有心理负担。”便伏在蜜蜡耳畔,“妈妈去做了个药流……”“——妈妈!” 妈妈安慰地笑:“日子还浅,没事。妈妈这不好好的嘛。”“可,叔叔知道吗?”“昨天和他说的。”“那,叔叔还不知道,妈妈就……”“他能理解。当初结婚我就和他商量好不要孩子,好好照顾蜡蜡。妈妈觉得,欠蜡蜡太多了。”妈妈轻轻抹泪,肩膀抖动着显得格外窄削——妈妈瘦了——从见面开始,这才注意到。蜜蜡感到指尖一阵紧缩的麻痹,这颤动一路传到心尖上。
赞赏
长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