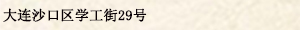在丹凤,那些年我们在老家吃过的杀猪饭好
原标题:爱吃
我自认为我是这世上最爱吃的人。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生,现在能记起的事情只能从七二年说起,我很笨,一点都不聪明,人常说三岁记到老,我呢……八岁以后发生的事才能记到老。
八岁开始上一年级了,已有两个妹妹了,每个妹妹间隔差两岁,大妹子六岁,小妹子四岁,和父母亲全家共五口人。那时是农业社生产队,父母常年在生产队上工,记得到年底决算父亲一天日工合二毛七分钱,母亲一天日工合二毛钱,到年跟前总共领回了一百五十元,我抱住我父亲腿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给买肉吃!给买肉吃!”。我有半年多没吃过肉了,上半年吃肉还是小叔结婚坐席吃了肉的,从那到年跟前在没坐过席没吃过肉。
年跟前有天后半晌,下庄子有邻家杀猪,庄子人们都去看,男人全都一身黑棉衣棉裤,壅壅肿肿,一半的男人腰里束条布腰带,也有两三个叔叔穿的棉衣那棉花絮串串从破烂处往外露着,腰里扎着一节草绳,熊着双手,脸色青黄青黄,目光呆板死巴巴的看着。那猪也可怜瘦希希的,毛又粗又长,我那爷说他喂了一年零两个月了。我站在人缝里,吓得用手遮盖住眼睛,可又把指头逢放的大大的,从指头逢看稀奇,只见在一张小方桌上,两个小伙压着嚎命叫的猪,见那杀猪匠肥头大耳,矮小粗壮,握刀的手翻过刀背,在猪头上使劲一磕,那长瓢嘴黑猪一吸气,脖子下陷一小坑,杀猪刀尖直捅进去,刀一抽,一股猪血冒浅着喷射而出,帮忙的人拿着事前准备好的盆子接血。猪四蹄乱蹬一会,噢呜呜喷扑扑的声越来越小了,……猪死了。我那爷黑瘦精干,取来生产队分粮用的大木杆称,把那脖子还滴血的猪用绳套住一称,环视一眼黑乌乌静视他的人群,又把牛蛋大摆动的称锤用手扶稳了一下,用手指把称锤系往回捻了捻,称稍立马蹶得老高老高,抬头扫了一眼庄子老小人们,十分豪迈地喊“15O斤重“!立马有人附和着说“是头大猪!是头大猪!是咱庄子这两年最大的一头猪”。也有人低声叽咕:“养了十四个月还能不大”。杀猪匠领着帮忙的人,给死猪经过烫刮除毛,又取来绳子,套挷住两条后腿,吊挂在场院顺横延伸的核桃树干上,开膛破肚,摘取下水,几道工序之后,杀猪匠用砍刀从猪正脊背齐刷刷砍了下去,成了两片子,晃悠悠转来转去,庄子大人们都凑了过去,围着看膘色,有人把手放在腰子眼的位置比划量量,嘁嘁咻咻议论着,我那爷的儿子喊到:“一指大些,二指少些,这是咱庄子最大的一头猪,膘色最好的一头,就按现在街上好肉价卖,一块钱一斤,谁要给谁先砍”。一时间庄子人有争着要,也有几位叔叔摇摇头嫌那太贵,悲催失望透了灰沓沓地,领着哭眉丧眼的婆娘娃下河走了,场子下河道路上传来了娃的哭叫声,紧跟着是大人的怒骂拳脚声,娃娃们又和刚才杀的猪一样嚎叫着,凄励的哭嚎如千万把刀子一样刺着人心,整个场院的人心顿然捏拿聚紧,喧闹吵杂转瞬即撾,霎时悄无声息,哭嚎声透过沉沉的夜空传遍整条山沟坡林。这件小事过去四十多年了,我每每走到那半枯死的核桃树下,仿佛又听到从河道里传来小时候小伙伴的嚎啕大哭声音,有次和儿子走到那给儿子说时,儿子说我讲的是童话故事,我又多么希望那是童话故事。猪杀对,肉卖完天已黑了一会了,两大堆篝火把一背笼的稍子柴都烧完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杀猪记忆最深的一次,活蹦乱跑的一头猪,在半晌时间,叫那杀猪匠就分成两片子,剁割成肉块块。称斤算两,记账掏钱,庄子割到了肉的人,嘻皮笑脸,娃儿们兴高彩列又蹦又跳,(我就是其中之一)摸着黑天黑地各自提回家了。
庄子割肉最大的一户是支书家,整整十斤,儿子在商镇公社工作,剩下的庄子人有割二斤、三斤.……我父亲割了八斤,每斤一元钱。我好高兴,往年只割五斤肉,我妈嘟囊了好几天,嫌那肉贵了,说有人在街上割肉才八毛钱一斤,又嫌割的多,我父亲说:“街上八毛钱的肉膘都没一指厚,这要一指半哩!我都量了几遍才割的,娃都大了,这年节多割些,咱屋一年都没割肉了”。
腊月二十杀猪割肉,肉提回家后挂在小房的楼橡上,我在外边在疯在野,一进门先跑进小房,两眼直勾勾的,把挂的肉瞅了又瞅,不觉地把嘴唇舔了又舔,我大妹子喊:“妈!我哥哥看肉都流涎水了”!我用手一摸涎水从嘴角都流到脖子了,用袄袖子围了围,脸一红,在我妹子头上敲打了一下,我妹子哇哇地哭开了,眼下流的是眼泪,嘴角还流着和我一样的涎水。
二十九到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二十九早上煮肉了,这一天是我一年中最勤快的一天,往灶火抱柴,拿扫帚扫屋里屋外,连养的四只来航鸡冒冒鸡都是我喂的,从柜里舀玉米人小个小够不着,都要支个橙子,把柜盖掀开用头顶着,才能用小碗把玉米舀出来。
锅里水滚了,我妈把洗好的肉放了进去,随着水滚蒸气腾腾,灶房里蒸气烟雾从门洞里、窗口里向外喷着。满屋散发着肉的香味,我姊妹三个扒在锅台上,翻腾浪滚的汤水把锅盖打的哧腾哧腾直响,溢溅出的油汤顺着我姊妹三个扒的锅台流到灶火,烟熏的眼泪都流了出来,烟呛的直咳嗽,我妈赶了几次叫出去,我姊妹三个没有一个出去,好象自已出去了叫那两个吃了肉自已吃不上了,大妹子把灶火的柴一根接一根向锅洞擩进,锅洞眨眼间就成了实实,我妈进来拉过我大妹子,又从锅洞把柴退了出来。我小妹子喊囔着:“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一句接着一句。我和我大妹子没喊叫,可在一直舔嘴唇,涎水从嘴角流出又用舌尖勾回嘴里,只听得喉咙咕咕噜噜地响。小小的肚子把整大锅肉都能装进去,空空的不得了。
肉终于熟了,我父亲捞到了盆子里,给我姊妹三个一人撕扽了一根筋骨,好烧好烧,啃咬一口,好香好香,赶忙换手,又啃咬一口,还是好香好香,满嘴油香味,筋骨上的肉不到十口就吃完了,用舌头把筋骨上的油舔净,嘴巴拌的啪啪响,对干筋骨棒棒看了又看,彻底是骨头棒棒了,才抡了出去。我妹妹吃完眼巴巴地看着盆里的肉,翅脚炸手还在要时,我妈说:“够了!够了!还有亲戚来,来了一块吃耶”!我妹妹甩手踏脚不行,我妈在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強行拽了出去,妹妹脚在地上划磨着,妹妹呜呜哇哇的哭开了,喊叫着“我还要吃!我还要吃"!泪水如雨漂泼,伤心地打着嗝。我父亲又给我撕扽了一根筋骨,白瞪瓷眼狼吞虎咽地啃吃着。
吃肉事过去四十五年了,我每每想起来,我对不起我妹子,小时候大人们重男轻女,吃喝穿戴都偏向着我,当时恁小,一点都不理会人情世事,到长到大人理会了,我那最小的妹子生了要命的病,在三十岁那年不在人世了,我心里常常思念,沉沉歉疚着,大妹子到现在还叫我“哥哥!哥哥”!童年时光的口语还没有改变。
赞赏
长按
| |